第一章
最初,初云被馆主神雁捡回来的时候,馆里从上至下都当是行善积德,回馈女神的照拂,何况小孩儿可爱得很,不怎么哭,瞪着乌溜溜的眼睛四处乱看。而且当时月树武道馆是一方名馆,每日钱去钱再来都痛快,谅也不差一个女娃娃的一口饭。神雁逗了几日就不上心了,扔给了尾树养。
尾树已经习惯了神雁的路数,边捏着鼻子用两个手指把站着屙物的尿布拈出来,边瓮声瓮气的问,“这熊孩子给起了什么名儿?我可跟你说好了啊,我养就得算我名下的人头,你起的不算。”
神雁远远的坐在楼梯上捂着鼻子,“你起,你起,随便你。你还当是新打了把剑呢?靠命名算主人啊。又不是带把儿的,要是带把儿的我还真当是宝剑给他正式起个名儿。”
尾树把尿布直接扔后院垃圾堆里,神雁嫌弃的说,“就数你会造,败家子儿,哪儿有你这么养孩子的,一条尿布就用一次,我可不出这钱。我就管一周一条的份儿啊。哎等等,这个尿布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尾树翻了个白眼,“你嫌花的多你他妈自己来养啊!你天天洗用一年都行!你先把自己的洗了去!你丫哪儿凉快哪儿呆着,站着说话不腰疼!”
神雁“嘿嘿”一笑,故意翘个兰花指,“孽徒!”他看着尾树非常不熟练的扯了新尿布来垫,发出感慨,“女娃娃就是不一样啊,我还记得你小时候小宝剑边跑边晃呢,一转眼都这么大了。你说这个女娃娃的胸能长多大?”
尾树咧嘴一笑,“能长吧,我刚打听了一个秘方,听说那谁家的小红就是吃这个长到……”,他挑眉用手比划了一下,递了个眼神给神雁,师徒俩互相“嘿嘿”一笑。尾树觉得手下绑得好像太紧了又解开了尿布重绑,果然已经有点儿勒出红痕了。
神雁又说,“唉呀妈呀,原来养个孩子这么不容易,我真是为她操碎了一颗心啊,日思夜想的为了孩子的将来反复思量啊,我都跟前面儿那条街的李婶儿说了,将来送到她那儿学女红呢。哎哟还有我的老腰啊,抱孩子都抱出病症来了,你瞧瞧,你瞧瞧。”说着站起来背过身要撩开衣服给尾树看。
尾树手下不小心猛地一用劲,结又打紧了,女婴开始半哭半叫唤,尾树没好气儿的解开结,“你丫闭嘴。你他妈才养三天!”他又瞟了一眼神雁,后者还撅着屁股,他一撇嘴,“师傅啊……你他妈又穿错内裤了。”
神雁扎起衣服,云淡风轻的说,“那是因为你把我的拿去当尿布了,不然谁稀罕穿你的。”他接着坐下,看着女婴不以为然的说,“只养了三天怎么了,我关心娃!我连她亲家都寻摸好了。”他眉飞色舞的说,“就咱馆里,新来的那个教枪的时彦,刚生了个大胖小子,我正打算去跟他说娃娃亲呢。”
尾树瞪了神雁一眼,“别扯淡,说好了我养的算我的人头,你别他妈给我瞎添乱,她嫁谁那得我说了算。”
神雁不满的“哼”一声,“那你倒是起名儿啊。不过我听着不痛快的不行。”
尾树最后毛手毛脚的打上结,后退了一步,欣赏自己的杰作,斩钉截铁的说,“就叫‘初云’。我想好了。”
神雁意味深长的看了尾树一眼。
最初,养着初云,馆里谁也没指望她能干点儿什么,任由她整天东跑西跑的自己乐呵。尾树没打算教她学个兵器,直到她第三次推倒了教枪的时彦师傅的小鱼缸,还不小心自己踩了碎片、流了血,就坐在案发现场哇哇大哭,金鱼在旁边直挺挺的甩尾巴,两条水草躺在一边儿。
尾树一边收拾残局一边想,是时候教初云剑术了。于是,尾树开始叮铃桄榔的砍树。
一个天如水洗般澄澈的下午,初春的风徐徐的飘着,带着微香在武道馆后院亦走亦留。尾树“呸”的往手上吐口吐沫,握紧斧子把树干劈成一块一块的木条,劈好的就堆一堆扔在一边,一会儿就干得汗流浃背,他又脱了外套扔在一边儿。初云就在旁边空地上小心翼翼的摆木条。尾树不时的看着她摆,不屑的说,“你个丫头片子能摆个屁啊,回头你尾爷教你摆美人儿谱。”
但是初云手脚利索的很快完工了,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跑过来拉尾树的衣摆摇晃,“尾尾树树,快快,快看我的字。”尾树一抬眼,就看见不远处空地上被摆了两个大字,“日你”。尾树把手上的斧子往树桩上一砸,撩起袖子拉着初云苦口婆心的说,“下回不准摆这个,听到没?我教你更有意思的。”初云眼巴巴的看着尾树,尾树在地上一笔一划的写,“日你。”
初云观察了一下,疑惑的问,“一样的呀?”
尾树叼着树叶说,“语音语调不一样,我写的这个重音在后面儿。”
尾树劈完木头,又买了锄头等工具,回来就在武道馆后面儿的空地上用木条圈了块儿地,然后开始翻地。
远京地广人稀,家家几乎都圈了地种地,但武道馆一直吃学费和倒卖兵器的钱,谁也不去干这个粗活儿。现在武道馆的钱吃紧,有点儿入不敷出了,尾树琢磨着开块儿地,正好种吃食,顺便让初云练练劲儿,不然学了剑术也是花架子。当然尾树还打着小算盘想着趁着初云有兴趣,自己能少干点儿少干点儿,尤其是初云要是熟练了,将来都不用自己种了,简直两全其美。
初云以前只见过已经长在地里的菜,没见过怎么种,觉得可新鲜了,一个劲儿要跟着玩儿。尾树一开始拦着不让,但拗不过初云,最后不耐烦的说,“让你干,让你干,但每天只准干半个钟头!多一会儿都不行啊。”初云于是倍加珍惜每天半个钟头的种地时间,尾树就叼着叶子坐在一边儿的阴凉处指导初云种地,“翻地要用力啊!走直线啊,我操你会不会啊,不行以后不让你种了啊!”
初云想学尾树双手握住锄头砸向地里、把表面的干土铲到一边儿,无奈锄头比她还高,又没劲儿,她就把锄头拖在身后来回走,跟尾巴似的,不时还左右晃两下,地上留下了浅浅的一条条土线,跟车轮子轧过的印子没什么区别。就这么折腾了半个月,尾树表扬初云,“我的小初云真棒!你看看,地都挖出一条沟来啦,以后奖励你每天可以种一个钟头好不好!”他蹲着摸摸初云的头,指着自己大半夜吭哧吭哧翻了好久的处女地。
初云有点儿懒得干,但是又觉得靠努力为自己每天的种地时间多争取了半个钟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犹豫了一下,用力的点点头,两个辫子都甩了起来。
尾树又开始坐在阴凉地儿指导初云种地,“……怎么种?哎呀反正就是土不是已经松了吗,你看着把种子埋进去就行!”
“埋多深啊?我想想……这样吧,这边儿这溜埋个你手那么深把,那溜埋两个指节就得了。”
“为什么啊?……啊对对,就是因为防止它们互相打架嘛,我们要给种子们创造相亲相爱的环境!”
“……隔一段儿种一点儿……啊对对,就这样,哎呀我家小初云长大了都会种地了!”
“对,这边儿种丝瓜,别搞错了啊,那边地儿才是种葫芦的……”
慢慢的,尾树把树枝捆的架子也搭了起来,像个小矮人的凉棚一样,初云在里面钻来钻去的,兴高采烈的自己跟自己玩儿,时不时的回头叫尾树也钻过来,尾树回一声不客气的“呸”。
既然种子都是初云种的,而且初云给她的地都命了名,这块儿叫“阿花”,那块儿叫“阿洛”。尾树教育初云说名字是一个咒语,一个象征,你既然给它们起了名,那地就属于你的了,你就得对它负责——于是接下来初云豪气干云,大拍胸脯,“我一定会对它负责!”,于是初云接着又接受了尾树对如何拔草、捉虫、施肥的指导,在春日灿烂的阳光里干得大汗淋漓,泥沾到了脸上,她也不在意。
尾树蹲在墙根表扬她的时候,她乐不可支把和泥浇水时偷捏的泥人儿举了起来,“这是初云云”,又举了左手,“这是尾树树”。然后她把两个缺胳膊少腿儿、还往下淌泥水的泥人儿按着一上一下的位置举高,“举高高!”
尾树叼着树叶说,“将来长大了,初云就不玩儿举高高了。”
初云想了一下,一溜小跑儿过来扑到尾树怀里。尾树嚷着,“手!手!拿开!妈【哔】全是泥啊我操!”初云从尾树怀里抬起头来,扬着一张花猫脸,认真的说,“要玩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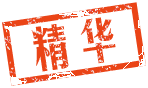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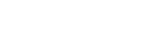









 发表于 2013-3-11 00:37:22
发表于 2013-3-11 00:37:22
 双倍卡
双倍卡 沙发卡
沙发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