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尔柏塔 于 2015-8-17 23:52 编辑
番外写的是爱尔柏塔她妈的故事【【【
出场NPC: 诺碧斯·亨里埃顿:爱尔柏塔的母亲 罗德尼·加西亚:爱尔柏塔的父亲
=========================================================================
Meine Rettung
——◇——
番外Ⅰ
诺碧斯想把煮糊的豌豆牛肉汤从火上端下来,当她的手指碰到烧红的铜质单柄锅的时候,瞬间捂着手指尖叫起来,她急急忙忙地找着清水,把手指泡进去。厨房散发着难闻的焦味,炉火尴尬地继续烤着锅底,把剩余的水分蒸腾成湿热的空气。
“妈妈……?”爱尔柏塔站在小小的厨房门口,扒着门往里看。
“别进来,爱尔柏塔。”诺碧斯从围裙里掏出八枚铜币,停顿了一下,放回了四枚,“去街角买一磅面包回来,好吗亲爱的。”
爱尔柏塔看着铜币的数量,疑惑地问道:“可是妈妈,你不是不喜欢……”——粗面包,爱尔柏塔把这个词咽下去,她记得母亲第一次吃粗面包时厌恶的表情,仿佛面包掰开时簌簌的碎渣都卡在她的喉咙里。
“这没什么,妈妈现在喜欢了。”诺碧斯把手从水里拿出来,被烫到的红斑鲜明地浮在她的手指上,连同其它的伤痕一起,刀痕,还有针尖的红点。这些伤痕原本不应该出现在她手上,她听着爱尔柏塔下楼的声音,颓然地蹲下,把脸埋进膝盖里。
她能分得清鱼子酱产地的区别的区别,分得清盛夏时哪个品种的葡萄酿的酒最醇厚,却无法自己亲手烤一块酥脆的面包。
她追着罗德尼的故事来到这海滨,却不曾见过故事里的海洋。
厨房的木板地面有一块被水泡的发胀,突兀地翘起一个角,诺碧斯看着翘起的地面,还有生锈的水管,突然哭出了声。
诺碧斯习惯了睡在柔软的天鹅绒大床上,塞满鸟儿绒羽的软枕被仆人晒得松软,而她现在每晚只能在冷硬的小床上辗转反侧。她在睡不着的夜晚看着木窗缝隙里透出的星光,怀念起了自己曾经种满红色蔷薇的窗台。那些花儿的花瓣浸满了柔和的幽香,干净得像女神的雕像。
她想起了年轻时与罗德尼偷偷见面的时候,罗德尼侧躺在在她阳台边的大榕树树杈上,含着叶笛。她因为没听过的音调,怯怯地从自己的阳台边探出头来,仿佛自己才是闯入静谧夜晚的不速之客。
罗德尼看到了她,却没有停止自己的吹奏,他看着她,专注地看着她,把来自自己家乡的歌谣完整地送进诺碧斯的耳朵里,然后含着叶子,对少女露出一个微笑。
“我叫罗德尼,罗德尼·加西亚,你呢?”
只是初见,却一眼许诺,诺碧斯溺死在那个不羁的笑容里,任凭自己淹没在爱情的洪流中,她明知道自己该嫁给谁,知道自己的后半生会在杯盏交错的虚伪宴会里度过——王都贵族家的小女儿,该在利益碾压的家族里安静地做一只漂亮的金丝雀,却在笼子的缝隙里,爱上了高空里遨游的苍鹰。
“可是河底有飘荡的水草,有漂亮的鹅卵石,还有多年沉积的宝藏。”她勇敢地说,为自己鲁莽的爱情做着想象中的辩护。
“他是父亲雇来的佣兵,没人知道他在为父亲做什么。”诺碧斯对着她刚插好的花束自言自语,“他就这么突然地来了,还经常来,打扰我休息了……我才不喜欢他呢,我可一点儿都不喜欢他,一点儿都没有。”
但她还是在夕阳的余晖里,把自己的头发梳得又柔又顺,并且“不经意地”忘记摘下自己最好看的耳坠。
后来,诺碧斯习惯了在月亮为蔷薇花瓣镀上银边的时候在阳台等待,罗德尼有时会来,有时不会。她就坐在自己的天鹅绒垫子上,靠着干净的大理石墙面等待着,觉得自己是歌剧里多情的少女,等待着她的爱情从树梢里伸出的手。
罗德尼会稳稳地踩着粗壮的枝杈,牵着她,把她拉到树干上坐着,她第一次坐在那么硬的地方。可是这触感多好啊,她想,粗糙的树皮在她细嫩的大腿上印出红痕。她甚至会在结束约会后,羞涩地用手指一遍一遍地顺着那些纹路抚摸,觉得这是夜晚为她留下的勋章。
“啊,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帅气的人呢。”她坐在他身边,谨慎地和他保持一个小臂的距离,然而这没能让她矜持多久,他们自然地靠近了。当她第一次把头靠在他肩膀上的时候,她紧张得连他在说什么都没听清,只记得自己的心跳,扑通,扑通,歌唱得像第一次飞出笼子的夜莺。
他告诉她很多事,很多她从来不知道的事,晓光的冰云桑葚要在未成熟之前采摘,情侣们在仲夏节的夜晚来到涌泉湖,燃起亲手点燃的水灯,蜘蛛路口第三个分岔里有家面包店,招牌是好吃得能把舌头吞下去的蒜烤面包。还有那些流传在夏维朗的关于乞丐的玩笑,森染脍炙人口的简单歌谣。
“多不可思议啊!”诺碧斯想,她也去过那些城市,但留在她印象里的只有最繁华的地方,数不清的礼节,还有千篇一律的问好。她走在那些城市里,就像看枯燥的编年历,而他却把那些年代剥离了,让那些最鲜活的东西跃入她脑海里,成了一整张地图——所有的东西都在动,人们在生活,小贩在叫卖,圣盾外的魔物在互相厮杀,她被这些平凡无奇的东西感动得热泪盈眶,吓得罗德尼笨拙地扯起袖子给她擦眼泪。
粗糙的衣料磨红了她的眼角,她却笑得比任何时候都开朗。
夜晚的树梢唱着来自天空的歌,那些旋律穿过梧桐厚实的叶子,让月光抚在罗德尼的脸上。诺碧斯看着自己的情人,他有着高挺的鼻梁,还有深陷的眼窝里碧绿的眼睛,他经常穿着亚麻的短衣和马靴,黑褐色的靴子包裹住他的小腿,看起来结实有力。
“等任务结束之后,跟我走吧,去我的家乡晓光,我在那里有个小阁楼,我们可以在那里住下来,抚养我们的孩子。”他把自己脖子上的黄铜钥匙珍重地摘下来,给她戴上。
她措手不及地羞红了脸,“孩……孩子什么的……”她支吾着,却下意识捂住了自己的小腹。
“他一定是个漂亮又乖巧的孩子,就像你一样。男孩我就教他学剑,还有游泳,那里的海是最美丽的海,夏天的浪花闪烁着钻石的光芒。女孩你就教她……”他有些疑惑地挠挠头问道,“女孩该教她什么呢,不过她只要像你就够了——”
她听着那些美好的,平凡的描述,忍不住想象着那样的生活,在读书的时翻页的间隙里,在看到新开放的郁金香时,那些画面总是不经意地闯入她的眼睛里,就像她真的经历过一样——要提着农妇们编织的篮子,去集市上买番茄和土豆,趁着阳光斜斜地照进厨房时,切块煮成浓汤。那些食材在火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她的丈夫推开门,带着今天赚的金币。他们的孩子蹦跳地迎接着回家的父亲,叽叽喳喳地讲述今天的所见所闻。他们坐在小小的桌子边吃晚餐,手肘碰撞时相视一笑。
她带着这样温馨的想象走进了厨房,想要学着做道口感醇厚的餐点,却被女仆们恐慌地请了出去——还附赠刚出炉的蓝莓蛋挞。
那真是最幸福的日子了,她怀念着罗德尼,那个帅气的男人,能轻而易举地把她抱起来,她永远记得突然腾空时自己的长裙飞扬的弧度,就像歌剧那样,她笑着抱住她的肩膀,任他抱着自己跳起华尔兹的脚步。耳间只有鸟儿的鸣啼和树叶的摩擦,她却听见了乐器合奏的华尔兹圆舞曲。
罗德尼即将离去的日子很快就来临了,跟着他开始一段新奇的生活,或是留在这里当一只老死的金丝雀,她丝毫不为自己充满偏颇的判断感到羞耻——“因为这就是命运啊!”
她忐忑地把自己最喜欢的枕头放进行李箱,小心翼翼地把他为她做的树叶书签夹在正在读的小说里,还有他们初见时她穿的那身拖尾连衣裙,那时她刚从舞会回到自己的房间,还没等她休息自己酸痛的双脚,就听见了露台外传来的奇异曲调。
然而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当然不会考虑到这种细节——女仆为她打扫房间时发现了床下的行李箱,她惶恐地报告了管家,管家在老爷的喝咖啡的间隙里,以一种淡定的,若有若无的语气,小心翼翼地提起了这件事。
她到现在想起来都忍不住手脚发寒,她的人生在这这个时间点上被完全撕裂,前半段是玫瑰与精装书籍环绕的闲适生活,她能用削尖的羽毛笔写出漂亮的字母游丝,而后半段……她用食指摩擦了一下自己手心的茧,硬得有些毛躁的死皮搔着她的指尖,就像父亲书房里的地毯一样,看起来有柔和的触感,却在真正抚摸的时候刺痛人的皮肤。
那真是个冰冷的夜晚,她忘不了那个地毯的触感,就像忘不了命运裁决的审判。
她的父亲端坐在书房,而她的爱人被人狼狈地押在了地板上。
“我给你卑微的工作以巨大的报酬,你却想要拐带走了我心爱的女儿。”她的父亲,一手把亨里埃顿这个姓氏写在金币后面的男人,用她没见过的陌生姿态,审问自己的情人。
罗德尼不甘地挣扎着,试图用自己的臂膀挣开对他尊严的侮辱,那太难了,两个侍卫坚定地扳着他的肩胛骨,他从凌乱的发丝里抬起眼睛,毫不畏惧地看着亨里埃顿:“卑微?哈?你们这些贵族见过魔物吗?见过苟延残喘的人们吗?你们肮脏得就像城市的蛀虫,心安理得地啃食着一切。我为那些战士们感到可惜,为了你们这群——连人都称不上的东西,让魔物的爪子生生插进他们的肋骨,你知道鲜血干涸的速度吗,还有闭不上的眼睛……”
“我当然知道。”亨里埃顿听着年轻人的顶撞,怒极反笑地打断他:“你以为鲁莽的砍杀就是勇敢吗,你天真得就像个小男孩。”
他不再言语,只是朝侍卫做了一个手势。
然而那个手势让诺碧斯血液冰冷,“不要!父亲!不要!”她扑进了书房,穿着她的睡裙,女仆慌忙地阻拦她,想要给她盖上块毯子。
然而什么都不能阻止她,她扑在了自己的爱情面前,像守护自己信仰的异端,毫不抗拒地把自己吊上十字架。
“你不能这么做,父亲!”
“他玷污了我的女儿!”
“我有了他的孩子。”
时间停滞了,女仆张大了嘴,管家露出他这辈子最惊愕的表情,场面像一场默剧,滑稽,却没人笑出来。
落地钟的钟摆摇晃着,秒针滴滴答答地走过,在大厅里形成回音。
“我怀孕了。”她又说了一遍,带着头皮发麻的一点羞耻,和不知从哪个隐秘的角落迸发出来的,她想象中的勇气。
亨里埃顿依旧端坐在他的高背绒面椅上,他的腰杆挺得笔直,这么多年来他面对过太多纠葛,那些困难不曾击倒他,只因他始终用这决绝坚硬的姿态走过险境,一步一步走上了家主的位置,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却在提起他时敬佩地说“那位了不起的亨里埃顿先生”。
而当他最疼爱的小女儿跪在他面前时,他却突然觉得自己老了,脊梁弯了。
他的眉头皱成山峰,雪山的风霜在他的山峰里挤压成厚厚的冰硝。
书房的蜡烛安静地燃烧着,诺碧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父亲手上有些褐色的斑点。她在这一秒突然忧伤起来,这个被她反抗的人,总是从他繁芜的文书工作中抬起头,把她抱在膝盖上,教她几个古老语系的单词,或是在她长大后,给她读一小段赞美诗。
“他老了。”诺碧斯想,尽管父亲依旧威严地坐在那里,从记忆的开始就坐在那里,但她突然觉得有什么变了,甚至觉得他有点可怜。
他的左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用食指缓慢地敲击着红木的扶手,缓慢得像他的心跳,或者是他身体里已经生锈的齿轮。
“多久了。”亨里埃顿在长久的沉默之后问到。
她看了看罗德尼,试图给自己一点勇气,然而她的脊椎沉重得像戴着三串项链,她努力地从自己的声带缝隙里发出声音来:“三个月……不,两个月,大概……”
“是吗……”亨里埃顿宽厚的手掌撑着眉头,阴影遮盖住他的眼神:“这个孩子可以没有父亲,但这个家族不能没有继承人。”
他说得很缓慢,缓慢得比时针的速度还要慢,但是又太快了,仿佛还未眨眼,秒针就已经走过一圈。
“家族想要立足在王都,必须要有足够光鲜的外表。他是一个平民,或许还是一个通缉犯,这样的污点不能留下。而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儿……同样是污点。”他眼神闪烁着,最后终于决断了什么,看着他的女儿,像看着即将被驱逐的罪人。
“这个孩子是家族的血脉,可以生下,再从其它城市的小贵族里入赘一个男人……”
“不!我不要嫁给别人!”
“你不会见到他,在你生下这个孩子之后,那个男人就可以消失。”
亨里埃顿决定了三个人的命运,在短短一分钟里。
“污点会被洗掉,洗不掉的,就给它纹上刺绣。”
哀求声没有任何用处,亲生女儿的眼泪也不能让他的脚步停顿,王都权利倾轧的齿轮碾得太快,他的家族徽章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裂痕。
那是个混乱而又有秩序的夜晚,一切都按照亨里埃顿的语言行走。罗德尼再也无法看见远方的飞鸟,而诺碧斯被养在远离主宅的小阁楼里,哀悼情人,自由,和只见过一面的,自己的孩子。
她在最美好的年华里被禁闭在了荒芜的堡垒,妊娠带来的痛苦根本比不上她内心的酸楚,她的爱人死了,她被父亲丢弃了,她的孩子不见了,她的心脏的血液都随着眼泪流干,却被空气挤压着,攥得她喘不过气。
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具枯壳,但在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时,总有一个声音在阻止她,她以为是自己卑微的恐惧,在这样的悲苦里出现的幻听,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五年。直到有一天,一个小女孩从围墙的草丛里钻出来,踮着脚,轻轻地敲响了她的窗户。
诺碧斯手指颤抖地把窗户推开一个小缝,那已经是她的极限,厚厚的木板在她住进这座小阁楼时就被钉死在墙上,她从牢狱的缝隙里看出去,几乎要掉下眼泪来。
小女孩穿着黑色的小皮鞋和高腰裙,和她小时候穿的一模一样。五月的末尾已经开始有了热意,小女孩掏出手巾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用稚气的声音对陌生人郑重地做着自我介绍。
“我叫爱尔柏塔,爱尔柏塔·亨里埃顿,你呢?”
【我叫罗德尼,罗德尼·加西亚,你呢?】
她捂住自己的嘴,巨大的狂喜让她膝盖都软得无法支撑她的身躯。她没有回答小女孩的问题,太久没有说过话,她觉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都很陌生。而那陌生的声音却不由她的一直控制,喑哑地,艰难地问出来:“你的名字,是谁给你取的?”
“我爸爸,不过他在我出生前就死了。”小女孩说,“外公告诉我,这是我爸爸在去世前,唯一给我留下的东西。”
她终于觉得自己活了过来,初夏的阳光是金色的,草丛里开着嫩黄的野花,小女孩站在囚笼外面,眨着和罗德尼同样颜色的眼睛。
“你叫爱尔柏塔·加西亚,我的孩子,叫做爱尔柏塔·加西亚。”她喃喃自语,跪了下去,她想抡起椅子砸烂窗户,又想放一把火烧毁这外墙,最后她扯着自己的头发冷静下来。
——“你以后,能经常来吗,我会讲故事,讲很多,很多的故事。”
——“但是你遇到我这件事,不能被任何人知道,并且绝对不能告诉你的外公,知道吗?”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EN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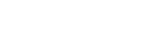







 楼主
楼主


















 发表于 2015-8-18 01:06:17
发表于 2015-8-18 01:0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