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帕西瓦尔 于 2016-3-16 21:27 编辑
三、敲响心音的协奏曲
Five little soldier boys going in for law; one gotin Chancery and then there were four. (五个小兵人,喜欢学法律,一个当法官,还剩四个人)
帕西瓦尔发觉自己站在一片纯白的迷境之中,他迷茫地四下里张望,却看不见任何事物的存在,它不像是地球上任何一处地方,仿佛隐隐有迷雾从眼前飘过,伸手却无法触及。
—嘿,有人在吗?
他刚想要开口发问,迷境却像读懂了他的心思一般,在那双紫色的眼睛里微微闪过白色的光芒,再熟悉不过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令少年的眼眶有些发涩,千言万语涌到了嘴边,悲伤、惊喜、期盼……情感源源不断地从心口喷涌而出,最终却只化为出口的两个字:“爸爸……”
面前的人拥有与他一样的银发,散漫地在脑后扎成一小束,嘴角边微含着浅浅的弧度,眼睛像天蝎座的心宿一般闪烁着艳丽的赤火,倒映着儿子的脸庞——与银发青年不尽相同,却仍带着稚嫩和青涩。
“你做的真得很棒,我为你感到骄傲。”
银发青年伸出手,放在儿子的头顶轻柔地摸了摸他的头,帕西瓦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僵硬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睁大眼睛凝视着早逝的父亲,生怕幸福的泡沫被自己碰碎:“爸爸,我这是在……做梦吗?”
“这需要你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银发青年的声线像葛尼梅得斯瓶中的清泉,静静地流淌,“排除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即使——”
“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那也是真相。”少年低声喃喃道,他抬起头,坚定地看向自己的父亲,“这是梦境。”
没有用疑问句,而是沉稳的陈述着事实。天才的青年警探温和地颔首道:“跟随你自己的推断便好。”他顿了顿,再度轻声开口道,“你在越来越接近真相,我的孩子,你有没有考虑过,身为幕后的人,会是你朝夕相处的人,你所爱的老师和同学,真相可能是残酷的……”
“我从不假设例外,例外会打破调查的原则。”帕西瓦尔坚定的目光中没有任何阴霾,“无论是谁。这是爸爸教给我的,我铭记在心。”
“那么找到了他们,你要怎么做呢?”
“法律会制裁他们。而我需要做的,是在尽量确保大家安全的情况下,将黑暗中的影子揪出来。”少年深吸一口气,他向父亲伸出拳,微微抵出,就像他们小时候一起做的那样,“正义是必胜的。”
银发青年微笑地伸出自己的拳,与儿子略小的拳碰在一起:“嗯,正义是必胜的。遵从你的逻辑去思考,帕西,你总是正确的。”
帕西瓦尔睁开了眼睛,下方传来的轻微鼾声告诉他室友的伊格学长仍在睡觉,显然天还没有亮。少年悄然地从上铺滑到地上,打开了小小的电筒,翻开自己的笔记本和从图书馆偷偷带出来的剪报,至今为止所有的线索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从笔中跃然纸上,每一个同学与老师的面庞从他眼前闪过,少年握着笔,冷静地分析起他们是敌人的可能性。耶米利昨晚在聚会上提供的新线索令少年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就像抓住稻草的溺水者,在茫然的大片海洋里,紧紧地攀住了那根稻草向岸上爬去。
艾薇安好奇地凑近了去看小碟子里精致的冷菜,九种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并排凝成一块,不提味道,光是看着便像艺术品一般,她的叉子停留在半空中半天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生怕破坏了漂亮的图形。半晌,她终于放下叉子问出了口:“帕西,这是……?”
“九珍蔬菜法式冻。”
“不,我是想知道你来学生会是为了什么啦,毕竟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听影烟老师说你昨天连晚饭都没吃,一直在图书馆翻过去的报纸和刑侦类的书本,并不是闲到能做法式菜来找我聊天的时候吧?”金发的学生会长拖着下巴,半开玩笑似的说道,“如果是为了找一位搭档,我已经有人选啦,你不如考虑一下我们学生会的万人迷副会长小秋,他还是空闲的哦,机会难得?”
“别拿我开玩笑啦艾薇。”帕西瓦尔苦笑道,他从昨天早上开始就一直在岛上四散奔波,根本没好好休息,不觉有些头重脚轻,连忙掩饰性地拉开桌旁的椅子坐了下来,“昨晚我听你哥哥说,你们似乎有一位远亲是十年前那个恶性事件的关联者,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艾薇安微微眯起碧色的眼睛似是在回忆着什么,又像是在忧疑,良久,她微微低下头去,轻轻地说道:“我的家中有一位阿姨,她曾经是一位非常开朗温和的人,但是她……后来似是发生了什么,家里人都不再提她了,大概正好就是十年前。”金发少女有些不忍地闭上眼睛,“等我再见到她的时候,是在一家精神疗养院里,阿姨她……已经疯了。”
“……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帕西瓦尔默默地点头,在老旧卫生间的所见如闪电一般在他的脑海中迅速整理了起来——血迹,十年前的师生大量死亡,艾薇家里精神失常的远亲阿姨——少年拍了拍好友的肩,柔声问道,“虽然有些失礼,但是我还想知道更多线索——如果有的话,我想要阻止你的阿姨曾经所遇到的悲剧重演。”
艾薇安握着叉子的手微微攥紧,令帕西瓦尔感到有些不忍,却也只能硬着心直视着面前的少女,他知道艾薇安是一位负责能干的学生会长,冷静、睿智、识大局——如果她知道什么,一定会筛出最有用的消息告知自己。
——除非她也是那帮人中的一位。那样,她所给的线索便要打上疑问的符号了。
沉默而凝固的气氛在学生会室里弥漫着,只剩下时针走动的机械声振动着空气,一下一下撞击着银发少年的耳鼓膜,敲击在他的心底。良久,金发少女开了口:“我的阿姨凯特蕾雅,曾经是绿林的一位保健医生,她是一位非常温柔漂亮的人,也是我最喜欢和尊敬的长辈之一,她就像我的母亲一样,直到我小学的时候,她的名字成了家中的禁忌。”艾薇安将手机的屏幕伸到了帕西瓦尔面前,那是一位消瘦得不成样子的女人,她躺在病床上,望向天花板的眼中透露着惊恐,尽管眉眼间还能看出女人年轻时漂亮的影子,却被岁月折磨得荡然无存,“我后来偷偷去看了她,兴许是时间足够长,阿姨的神智大部分时候是很清醒的,只是偶尔,她会忽然说出些无法理解的话。”
“无法理解的话……?”
“‘他们来了!’、‘不是我,跟我无关!’、‘放过我吧!’之类的,阿姨她,像是在害怕着什么人会找来。”艾薇安合上了手机,双手交握在桌面上,“她是一位意志非常坚强的女性,我无法想像是什么事情能让她变成这样,即便我进入了这所学校三年,也无法凭自己的能力查到水落石出,唯一知道的便是当年的学生都是2A班的人——如果是帕西的话,说不定你可以做到。”她露出清浅的笑容,拿起刀叉切下一小块法式冻的边缘,“这也是我的请求,我想知道发生在我亲人身上的真相,拜托了,帕西。但也要注意保重自己——你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是没有好好休息吧?能从将近两年份的报纸里翻出那样小的一块消息一定很费神了,小秋他很担心你。”
“没有时间休息。”帕西瓦尔有些烦闷地揉了揉眉心,撑着桌子站起身,“我相信这所学校无时无刻不在危机中,谁知道哪天我们疯狂的敌人们就会引爆炸弹呢?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流逝。”少年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托着腮问道,“你刚刚提到当事学生都是2A班的,对吗?说起来,我记得2A班很久以前换过教室,校方的说法是教室老旧不能再用,但同样是教室,其他的却没有更换……我知道了,艾薇,学生会有老教室的钥匙吗?”
“嗯?啊,有的,你要去调查吗?”
“我无论如何都很在意为何要更换教室。”银发少年肯定道,“我要去看看,说不定那里会有我想要的答案……唔!”
“帕西?你没事吧……?你不会连午饭都不打算吃就先赶过去吧?”
艾薇安担忧地看着扶着额头差点摔倒的同窗,刚要说什么,却被帕西瓦尔笑着阻止了:“不用担心,有点没睡好而已,我一会儿回宿舍休息一下便好——将钥匙给我吧,不要忘记吃法式冻,那可是我的自信作。”他从艾薇安的手中一把拿过钥匙,挥了挥手,便快步走出了学生会的大门。
旧年的2A教室与那间被遗弃的洗手间一样散发着令人不大舒服的压迫感,凌乱的课桌椅有的倒在地面上,有的缺少了一个腿歪斜在一边,也有的上下颠倒放置着,这条走廊也显得格外寂静,尤其是在现在危险的时段,没有人敢来到这里。
每个有些年代的校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校园传说,绿林自然也不例外。自己活动的人体模型、夜晚会看到鬼影的老旧厕所、在树下亲吻就能爱情长久、鬼压床的保健室……以及,这间神秘的老教室。
“我好像听说过去有人在这里失踪过……不过也是臆谈,没有确实说法。还有说这里会听到冤魂的叫声……世界上是没有灵异的,这里看起来确实发生过大事件。”帕西瓦尔自言自语地喃喃着,这里的电同样已经罢工了,甚至连电灯的电线都已经露出,摇摇欲坠地挂在天花板上,他只能拿出手机打开自带灯光进行照明,“6%的电量吗……看来撑不了几分钟,要抓紧了呢。”
少年微微扬起电筒,墙上的水泥已经剥落,却不难看出墙上有刀片划过的痕迹,显然是经历了相当的破坏,这点从凌乱的桌椅也能看出。原2A的教室仿佛还保留着事件发生的时刻,倘若闭上眼睛轻嗅空气中些微的血腥味在脑中模拟它曾经的模样,能不能想象出案发的现场呢?
他晃动着手电的光,凝视着墙上地上隐约可见的各式血迹,尽管它们早已干涸,却仍向帕西瓦尔哭泣着诉说跨越时空的故事。年轻的小侦探在心里迅速地列着血迹可能对应的死法,然后,他抬起头,看见了墙壁上令他在意的一行字。
与其他的暗红不同,唯独这行血字仍富有充满生命力的鲜红,尽管已经有些干涸,却仍挡不住它年轻新鲜的色泽,显然是在不久之前写上去的,这个发现令帕西瓦尔浑身血液都凝固了。
——有人不久之前来过这里,写了血字,会是谁,又为什么要这么做,用的,是谁的血?
“Prisoners behind the bar……how do you plead……庭上的罪人,你可知罪。罪人,指的是,谁呢……?这是警告吗?”少年小心翼翼地辨识着上面的字体,伸出手去想试试血液的凝固程度,下一秒,他的视野却忽然失去了光源。
手机的电源耗得一干二净。这令他有些后悔,他不禁在心中计算着跑回寝室充好店再回来需要多长时间,又不甘心地凑近了去,想要发现更多细节再离去。
身后忽然传来的物品碎裂声在全神贯注思考的帕西瓦尔耳中犹如炸雷一般,惊得他猛然回过头去,心脏疯狂地撞击着胸腔,一瞬间所有他听过的关于这间教室的怪谈冒上心头,少年一边在心中不断喊着“不会吧不可能啊”一边按紧了胸口试图阻止突如其来的急促呼吸。借着窗外依稀的阳光,他勉强看清了地上迸溅开来的是电灯的碎片,而教室里空无一人,只有他自己站在原地。
除非还有人躲在阴影里不想为他所见,还是说只是老旧的电线被时间的洪流折断。
帕西瓦尔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倾听着教室里任何细小的声音,高度绷紧的神经令他努力忽视的眩晕感愈发严重起来,可他无心去照顾,只能握紧手中的手机,脑海里冒出了无数种遇到意外时逃脱的方案,却还是没有轻举妄动。
半晌,逐渐适应光线的帕西瓦尔终于确认了自己的安全,单纯是电灯过于老旧而电线绷断罢了。他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却在下一秒钟膝盖一软,身体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
——不行,再撑一会儿啊,他还不想,在这里倒下……!
银发少年攥着胸前的衣料拼命想要撑着旁边的椅子站起身来,眼前的黑暗瓦解了他的全部意识,就连少年的意志也无法反抗身体过度疲劳做出的自然保护,在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刻,他忽然感觉到地面是那样冰冷,远比他所想象的要冰冷,那种感觉顺着他的骨髓爬遍全身,让他无意识地打了个寒噤,朦胧中,他仿佛听见有人用惊慌的语调呼喊着自己的名字,少年想要应答,神智却被黑暗迅速地侵蚀,便很快什么都不知道了。
“咦,这就是帕西的家?”
“哇、等等、我以为是克雷尔来了怎么是你?!”
一向沉稳的帕西瓦尔难得露出这样慌张动摇的神色,本能驱使他飞快地将门在身后关上,背紧紧地靠着门,在乌秋眼里简直像受惊的雌鸟护着雏鸟一样,莫名的露出了可爱的一面。
想将对方吓一跳的计谋得逞,乌秋带着狡黠的笑容托着腮,语气也不禁微微上扬:“我到小克家里去印资料,想起你跟他住得近,就不请自来啦。怎么,没想到我会来?”说着,他微微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借着没完全闭合的门缝向里望去,“唔,不让我进去坐一下吗,帕西同学?”
帕西瓦尔难耐地低下头,咬紧下唇犹疑了起来。这样的神情对于乌秋来说是十分陌生的 ,那是他所认识的那个少年不会露出的神情。
半晌,帕西瓦尔终于抬起眼,他打开身后的门,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嗯,乌秋……请进。”
这是一个从小到大便拥有温暖家庭的乌秋所无法想像的冰冷房间。它只能被称之为房间,是因为它没有丝毫“家”所拥有的元素。房间里整洁得异常——除了因为帕西瓦尔是个严谨的人,更因为家中基本没有什么物品,也丝毫没有第二个人居住的痕迹,只有一套孤零零的餐具摆放在洗碗槽中,显然是刚吃完午饭。
“唔,还好小克常用的茶杯还在……乌秋,你要喝英式绿茶,还是立顿红茶?”帕西瓦尔背对着乌秋弯下身打开碗柜,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若无其事。良久,他发觉乌秋一直没有出声,不由得回过头去,“乌秋?你要哪种……”
“帕西你……一直是一个人吗?”黑发的少年看向他,眼神中充满了惊讶——与帕西瓦尔所无法认出的更复杂的情绪——乌秋不由得走近了房间的主人,他感觉得到这里从每一个角落散发出冷寂的气息,“你家里的——嗯——其他人呢?”隐隐的预感在他的脑海里叫嚣,尽管他刻意想去忽略那种可能性,可那双紫色的眼睛黯淡了下去,像是在肯定自己的猜测一样。
“乌秋,我……”帕西瓦尔深吸一口气,将茶杯放在餐桌上,直直地看向面前的少年,“我的父母早在我上初中之前就不在了,我现在是一个人住,生活费是母亲家里的亲戚每月打给我,所以我才去考绿林的……因为不想麻烦其他人。”
“……很抱歉听到这些,帕西,我……不是故意要闯进来的,我只是想着认识你这么久又同城却没有打过招呼……”
帕西瓦尔看见乌秋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有些失措的模样,不由得微微一笑,拿起茶壶斟满了茶杯,放到了乌秋的面前,温和地轻声说道:“请不要难过,乌秋。我从不觉得这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这是既定的事实,既然已经至此,我便要自己走剩下的路——在学校里不说,只是不想去张扬。”
乌秋似是要掩饰自己的失态一般拿起了桌上的茶杯,可握着茶杯的手却紧紧攥着小巧的杯子,他感到自己闯进了一个不该知道的秘密,银发少年的笑容下所隐含的寂寥让他的眼眶有些发涩,不禁拍上对方的肩,低声道:“有什么事情不要自己一个人扛着,偶尔依靠一下朋友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愿意,帕西,”乌秋回望着那双他看过很多次的堇色双眼,它们总是闪烁着冷静与睿智的火焰,像启明星一样引导着自己的心,“我总能做你忠实的听众,这件事情我不会跟其他人讲的,就当作一个秘密吧。”
——黑发少年一直被大家所围绕在温暖的中心,他想将面前的人拉进来,让帕西瓦尔也能暖起来,而不是被遗落在冰冷的角落自己取暖。
而他也做到了。
当乌秋背着昏迷在旧教室的帕西瓦尔飞奔向医务室时,他感受到背上的人因为体温过高而无意识地发颤,即便隔了外套也能感到银发少年的热量在透过衣料传来,他不禁加快了脚步,在心中庆幸了起来。
还好他找到了他。
这一次,他还是找到了他。
Four little soldier boys going out to sea; a redherring swallowed one and then there were three. (四个小兵人,下海去逞能,一个葬鱼腹,还剩三个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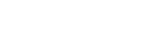









 发表于 2016-2-17 15:40:09
发表于 2016-2-17 15:40:09










 楼主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