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修·德米安 于 2020-11-29 23:21 编辑
【4】
他一声不吭地冲出去。向着那个高大可靠的背影跑去,浑身沾满干草、兔子窝的气味。
月海转过身,年幼的男孩迎面扑来,捕风的斗篷在其身后荡扬。毛茸茸的金发蹭到了月海的腰际。
“您这是怎么了?修伊少爷......”他抬起手,看到揪着自己衣襟的小手上浮现淤青。 “谁又欺负您了?”
抬起的手掌轻轻放下,慢慢揉着男孩的头。 “还是不肯说吗?” 他蹲下来扶住男孩,宽大的手掌几乎要包住男孩的肩膀。男孩仍垂头揪着兜帽,不肯露脸。
年仅五岁的少爷身上总会莫名出现新伤,这让初为人师的月海非常担忧。 “我教给您的格斗技,没有派上用场吗?” 男孩摇摇头。
“对方有几个人?” 男孩撇开头。
“您该不会——又没有还手吧?”
月海充满砂粒感的厚实手掌伸进兜帽、捧起了男孩湿润的脸颊。而男孩只是眼睛低低地看向一边,挂着正八字的眉毛,微弱地抿嘴笑。 “月海叔教给我的都很有用——只是,一旦面对他们,一旦面对他们‘倾诉’的那些无法排解的苦难......我、我便无法动手了。” “因为、我是阿尔洛人,我是贵族,所以......” 声音越来越低落。
月海旋即在脑中锁定了‘犯人’。久居深宅的少爷在他的照看下,不曾踏出过宅邸半步,所以要排查出少爷所避嫌的对象着实容易。 他静默地看着因为拘谨而蜷缩肩膀的男孩,拇指轻轻地摩挲他的双肩,思忖着。 “您的性子实在太柔和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没有人该无端受到伤害。”
扑朔的绿眼睛倏然睁大,又迅速看向一旁,“我并不是因为受到伤害而感到难过......” “他们——生来也并没有做错过什么,可是却......”
“而且......攻击别人时的触感,非常,非常糟糕。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也请您,不要去惩罚他们......好吗?”
沉默增殖。
大约是在认知刚刚成型的时候吧,当世界被森严而又粗略地划分出区别,普世用以衡量价值的观念即为年幼的修带来认知上第一次名为矛盾的撕裂。从此他的良心开始备受煎熬。 六岁那年的兼济期间,夏维朗的德米安府邸陆陆续续接纳了十几个新仆人和一对朝灵。小少爷一直以来被教育信仰的美德使他对待每个人都无比温柔与宽容,可单纯的心性也将他推往了阴暗的边境。
微弱的风拨动着金黄的发丝,午后的阳光暖烘烘地渗透进衣料。云移的斑影倒映在男孩脸上,如光透过温润的水珀。
直到一点温凉的水珠掉落在月海的手指上。 “好奇怪啊,为什么会......”男孩开始愈来愈剧烈地揉着眼睛,兜帽向后滑落。
“修伊少爷,我希望您能明白。” “您的忍耐并不能真正消解他们心中的伤痛,而恰恰会使之变相为另一种施暴。”月海轻轻抚摩着修单薄的背。 “况且,如果大人的罪过都要让小孩子来承担,那么不论是向你索取补偿的大人还是逃离所应背负罪偿的大人,都太失格了啊。” “我是您父亲选定的护卫长,更不能允许有人伤害这样的您,同时,我也希望您能更加坚韧,并把这份可贵的美德传承下去,所以——” “请您安心地、自由地长大吧。”
淞玉收回营业门牌准备下班时,修抱着两个大牛皮纸袋回到店里。撒了雪白糖霜的长棍面包与欧芹的菜穗露出半截。农夫拉孔扎伊的儿子涅宁,每天都会在清早牵着驴子涅石进城分送货物,顺路把修长期订购的食材寄存在双塔巷巷口的陶器店。
外面的天色正是昏黑却又还能勉强辨清建筑轮廓的时候。尼恩格兰下城区的街市渐次点亮繁荣喧嚣的光源。但在幽深的双塔巷尽头,这家静默的小店已早早隐入了安详的黑暗之中。
两人没有点灯,淞玉只熟练地锁了店门,沉默地跟在修身后进了里间。 里间的西边是通往二楼的木梯,东边则连接着带有地窖的厨房。房间正中堆放着装满香料的木箱。修将纸袋堆放在厨房的方桌上,凭记忆摸到了前夜留在抽屉里的半截羊油蜡烛。屋内的物件这才骤然现形。 这时,这家用沙漏形浮雕作店头标志的货铺,正式进入夜晚。
用手指细心揉洗去菜茎间的泥土时,伴随着乡野的气息,修总会想起儿时那双温柔又带着薄茧的手。那双手会利落地择去萎靡发黄的烂叶,将蔬菜去根切段。 案板发出“梆梆梆”的悦耳声响,洗净的牛肉也就被整齐切块,和冷水一起入锅,等待沸腾。记忆中的最后一餐没有昂贵的牛肉,有的只是田埂间股股生长的植物块茎,但那仍是一顿令修难以忘怀的晚餐。 接着是修很喜欢的、用汤勺撇去浮沫的过程。仿佛杂绪也能随着不断膨胀的浮沫一同被剐去,只留下心底最纯粹的菁华......
自修考入国高之后,就再没能见过那双手的主人。 修与母亲阔别已八年了。一半是父亲的禁止,一半是自身绕不过的结——他不是没有回过尼恩格兰本家那座祖宅,只是他再无法靠近那间阁楼半分。那是一座承载着修童年一半幸福一半伤痛的记忆遗址。与此同时,修对敲门产生了无名的抗拒。如果可以,他宁愿提亮声音向屋内的人问候,以征求许可。就像他从来不会主动道别,回避着讲出每一个包含“再会”之意的语句。在人们纷纷向他挥手离去时,他只会轻轻点头,固执地不提那句话语。又怕给人冷落的印象,于是呆立在原地,竭尽所能地怀抱真诚,目送着每一个背影,久久,久久。 ——「また明日」(*明天见)
捞出熟软的牛肉方粒后,向汤里拨入一半片好的红菜头与胡萝卜,和着适量砂糖与盐搅拌均匀——那时在那间简陋的农户厨房里,母亲也是这样提着试味的汤勺,随心畅谈着异族的料理。卷心菜、洋葱、干红海椒......煸炒至一定程度后加入白醋与香料束,再待汤汁红旺加清水焖煮。年幼的修伊很喜欢用葱白卷起来的香料束。
烹饪是这样自由的一件事情,只要摸索出门道,任何食材都能充分发挥出独特的味道与价值。而且这种美好所带来的感动也是无界限的。所以母亲喜欢烹饪,喜欢阿尔洛和朝灵的料理,以及此间所生的故事与文化。修也喜欢。
将中午出门前就炖好的肉汤置于旺火上,切入卷心菜和马铃薯片,接着倒入方才焖好的菜汤。热气扑面时,修偶尔还是会不争气地鼻酸一下。尽管明知寂静昏暗的四周旁无他人,却还是会别过头去,使劲眨眨眼睛,或是干咳几声。
每一晚都是一次离别。母亲的真实便是在那一晚的道别后消失在了夜色中。 修如何不会揪心。他重复着每一道步骤,却无论如何找不回那时的味道。那时的他还未有现在这般身长,几乎仅与灶台一般高,还不能轻松地提起锅盖。这时母亲会捏着蒸布,揭开热腾腾的汤锅,在一片白蒙蒙的水汽中笑语。
揭锅后就可以做最后一步调味了,修特意在不加辣椒末的那份汤盘里多加了白醋与牛肉粒。最后淋上特制的酸奶油。 第一个教修朝灵语的人其实是他的母亲。而他学会的第一句朝灵语是道别。
森染风味的红菜汤煮好后,修换了煎锅,又切了半块黄油搁上火。他后靠着长桌,静静地看着黄油在锅心一点点变小。 决定报考国高的那年,从修身边离去的不止有母亲,还有师父。待他如亲子的师父。 那是在修将近六岁的那个兼济期里,出现在父亲身边的一位侍从。看起来面容尚还年青,发鬓却已早早斑白。一位被唤作“月海”的朝灵剑术师。 那是个非常少见的、在短期内就获得了家主古斯塔夫·德米安信任的人。 他忠诚地负责起了宅邸的安保工作,同时也代替德米安勋爵教导、照顾着修。
锅面将要冒烟,修把方才余下的牛里脊肉平整地排列在锅面上翻煎。肉质中的水分滋滋作响着蒸发,而浓香会被留下。 月海并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哀悼之处,消失得无踪无影。修曾向冷淡的父亲表达悲愤与不平,他以为月海是父亲的亲信,所以至少......可家主并不打算对此解释什么,恍若世间从无此人般地,继续着他日复一日的繁忙要务。修不是不明白世理,只是这样一来,他就更加不理解父亲还在乎什么。他究竟在为何而忙碌。
修有些不快地向锅里倒入了一大碗肉汤,心不在焉地收汁后将肉排装盘、盖上保温盖。随后迅速将一旁焯过水的马铃薯角过油炸至金色,沥尽余油后撒盐与欧芹拌匀。 而每当眼泪沥干,惘然回首过往的时候,修会隐约发觉,月海师父的“离去”其实充满着预兆。身体挥之不去的倦意为这个朝灵男人染上鸦青色的忧郁,如同病疾笼罩的隐喻。以及持续不断的头痛、愈加苍白的鬓发,或许还有时不时的钝滞与失神,始终看不清的过往梦魇,和越来越频繁地叫错淞玉和修的名字,还比如......梦呓般地呼唤自己的名字。 在肉排的另一半铺上薯角,切碎两三支罗勒装点,撒上些许洁食盐与粗磨黑胡椒粒,再浇上软化的奶油香菇洋葱酱汁——其中花生油与瑰丽酒的鲜美会融为一体,飘散开来。
——究竟为何会呼唤自己的名字呢?
修假想着自己每一份珍贵的记忆也会如同这香味般散失于风中——是不是若不努力抓住些什么的话,最后就连自己本身的存在也会忘记(消散)?
紫甘蓝与苦菊、蜂蜜醋与蛋黄酱,草草搅拌成沙拉。紧接着浓郁香甜的时茵玫瑰甜点也出炉了。点上亮晶晶的晓光特产盐花,修熟练地端起大大小小的餐盘,顶着烛灯,缓步踏上二楼。 两年前他们搬进来的时候,二楼的隔墙就已经被拆除,两个幽闭的房间合为一个宽敞的大厅。和冗积着货物的一楼不同,修只简单地布置了几套书橱与储物柜,在正中央摆上长桌,只有在夏日举办茶话会时,才会换上圆桌。环厅四角摆放着盆栽,墙壁上只有几幅挂画和用于收藏的装饰剑。哦,还有淞玉钟情的蹲在壁炉边上的老沙发。 此时淞玉坐在长桌远离楼梯的那端尽头,桌上摆着环形的迷你轨道。修将手中、肩上、头顶的餐碟和烛灯平稳置于迷你矿车、双驾马车、以及小雪橇所拉的拖车托盘上(原本还有一队雪橇犬,上上个月被派遣出去“护送”塘底的孩子们回家了),随后拧动这端尽头的机械发条。伴随着叮叮咚咚的八音盒奏鸣,小车平稳地载着货物,驶向前方。修就坐在长桌这一头。 淞玉没有就今夜格外丰盛的晚餐发表感言。修也不意外。他们总是缓慢、静默地一同进餐。
修很享受晚餐的时光。早餐无论多早爬起来做好,进餐时心里也仍会多少带着匆忙之感,而午餐是昏昏欲睡的兄弟。只有晚餐不同。唯有在经历了一天的劳作、带着疲乏的安心将一天整理、圆满结束于烹制晚餐的过程中后,他才能任由思绪在恬静的黑暗中发芽蔓延。 这和在塘底的晚餐也不同。在池塘之底,修时常在热闹的间隙中突然“脱离”出来,他会惘然回望四周,发觉只有自己的耳朵关上了屋门。他看到每一张小嘴中分享的形色见闻都会不断升腾、升腾,汇聚在热热闹闹的餐桌之上,积冗在略微闷热的天花板之下,而后杂烩作另一桌丰盛的晚宴。而他触摸不到。 他也不想举起餐叉。
回过神时,淞玉已经开始收拾餐盘。 在修眼前,漆黑的长发从少女的肩头滑下。朝灵少女俯身轻盈地把碗盘堆成一叠,而修的目光停滞在让他产生抚摸冲动的黑发上,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意念还是真的有发出声音道过一句“辛苦啦”,只是呆呆地继续他朴实的臆想。 儿时的修时常对月海近似早衰的发色感到担忧。他曾醋浆煮豆,为师父染发,又扒出在藏书阁深处发现的破旧药典,啃着词典校对配方,生怕出一点差错。最后凑出四味药材,请管家到中央药房抓来研磨成粉。又每日偷偷早起去打清晨初汲的井水,兑汤药与师父喝...... 只是纵使亲手为师父染上象征年青的色彩,修也仍能隐约察觉到师父内心中有一片土地正在迅速地衰老。师父一天比一天疲惫,皱纹一条一条侵占他的肌肤。隐秘的病灶如同一个空洞,正一点点夺走他的师父。
“月海叔,为什么总是看起来很累呢?” “我吗?” “是啊,你现在看起来就很疲惫啊?是因为总是睡不好吗?” 月海遥望着黄昏的天边,男孩叫他,他便摸摸男孩的头。男孩拉拉他的袖子,他便蹲下与男孩平视。他看到男孩眨眨眼,似有光晕落在那双祖母绿的眼睛上。朝灵男人茫然地思索着,仍然凝视着远方,最终慢吞吞地吐出一句开脱之词。
“或许是我习以为常了,所以才会忘记疲倦......”
直到现在修仍未忘记那天,当他顺着师父的目光望去时,他看到了从尼恩格兰升起的月亮。
————
拉孔扎伊,住在尼恩格兰城外的农夫。是个鳏夫。
涅宁,农户之子。不种地。曾为陶匠学徒。现在自己家里鼓捣陶器工坊。一次进城与修相识,两人很谈得来。
涅石,一只黑驴子,是涅宁的老朋友。名字也是这位老友起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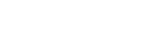










 发表于 2019-7-9 07:17:22
发表于 2019-7-9 07:17:22
 双倍卡
双倍卡 沙发卡
沙发卡 楼主
楼主







 终、终于——!我也不说什么终于了总之是那个终于!(防言出法随flag隔天成立用)
终、终于——!我也不说什么终于了总之是那个终于!(防言出法随flag隔天成立用) 大丈夫だ 问题ない修先生!理解理解!——by三年5K字选手。
大丈夫だ 问题ない修先生!理解理解!——by三年5K字选手。 其实说实话,我姑且还是知道自己为什么看不下去的。哎也不能说看不下去,准确点说,大概就是那种,自觉地不再继续的行为还是有一个缘由的。并不是那种比较严肃的问题,毕竟谁能就看三行就看透一篇呢(。),于我最大原因还是,怎么说好呢,我比较难概括一些情形啊事物的(看看上面这些破碎的发言!),平铺直述巨白话来说是我不想受到太多的影响,因为我也有想填的坑,然后《疯月亮》这个开头吧,就很符合我的波长(?)很容易一下子就沉浸下去……对比很多沉浸不下去而没办法继续看的东西来说真的是有够冤枉的XD
其实说实话,我姑且还是知道自己为什么看不下去的。哎也不能说看不下去,准确点说,大概就是那种,自觉地不再继续的行为还是有一个缘由的。并不是那种比较严肃的问题,毕竟谁能就看三行就看透一篇呢(。),于我最大原因还是,怎么说好呢,我比较难概括一些情形啊事物的(看看上面这些破碎的发言!),平铺直述巨白话来说是我不想受到太多的影响,因为我也有想填的坑,然后《疯月亮》这个开头吧,就很符合我的波长(?)很容易一下子就沉浸下去……对比很多沉浸不下去而没办法继续看的东西来说真的是有够冤枉的XD
 特别喜欢这种少女悬空感!(?)
特别喜欢这种少女悬空感!(?) 最后这段写记忆和情愫真的很美,我很中意!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有看过说每个人思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科普,我自己是,阅读和写作的时候脑子里是会有声音的……或者说自己会念出来?默念?所以更喜欢那些至少不绕口,最好顺口的句子。虽然有些字作为没文化の代表我并不会读!(理直气壮)但是因为断句和长短句都很舒服,就那样默读了过去,就觉得是非常好听的回响。
最后这段写记忆和情愫真的很美,我很中意!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有看过说每个人思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科普,我自己是,阅读和写作的时候脑子里是会有声音的……或者说自己会念出来?默念?所以更喜欢那些至少不绕口,最好顺口的句子。虽然有些字作为没文化の代表我并不会读!(理直气壮)但是因为断句和长短句都很舒服,就那样默读了过去,就觉得是非常好听的回响。
 其实这里有点……怎么说呢,从下面的描述来看德米安们好像是慈善家属性?,至少心地不会太坏?但是古斯塔夫先生又对妻子很无情的感觉……还是没到他的视角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呢?
其实这里有点……怎么说呢,从下面的描述来看德米安们好像是慈善家属性?,至少心地不会太坏?但是古斯塔夫先生又对妻子很无情的感觉……还是没到他的视角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呢? 修先生果然是柔软好少年!
修先生果然是柔软好少年! 给安安静静努力更新的修先生花花!
给安安静静努力更新的修先生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