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玛尔钦 于 2017-12-31 01:00 编辑
S.399
◍ 拾贰 ◍
“新来的大哥哥,你又欺负刺客姐姐了?” “我没有。” “可她见着你来就不说话,死盯着你看,你说是什么事嘛!” “你真要我说?” “你说嘛?” “我不说。” “哎——”
十二、物换星移几度秋
凡尼纳德打他身后走过来,边走还边揉着脑袋,看起来格外疲倦的样子。一瞅见那灰发的少年,方才还口无遮拦叽叽喳喳的姐弟俩立刻噤了声,脸上亮得通明,冲凯特小少爷灿烂相迎。他得了个机会,趁机绕过两人把手里的饭食拿进屋里。推开门,床头坐着个女孩子,新雪的白光打窗玻璃照进来,将她整个人拢在光里,像是在这冰雪消融的暖意中兀自披了层霜。他带上门,在桌前取出他们的午餐,于是那女孩儿就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瞧,瞧到兴头,就笑,一笑起来整个人又清淡了三分,像是随时要化成雪片,眨眼便无迹可寻。 时茵入了冬,霜雪一场接着一场,从屋檐庭院到发梢肩头都落满了蓬松的晶莹雪屑。这些新雪还未被人拿鞋底碾过,大道上撒的粗盐粒也没落进凯特宅的门槛,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正是初冬最美的时节。 随着最后一阵留恋的秋风提起裙摆登天而去,被一同带走的还有长久以来盘旋在大宅上空的焦躁和不安。那天夜里无来由的战斗像是绷紧的弦骤然断裂,弃了琴,许多事情也就迎刃而解。 要说其中最重要的,一共有三件:
第一件事情,是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刀。 这么说或许有些奇怪,毕竟他一直背着那柄长刀,小小的身板拿刀稍微矮了些,走路不住神就会敲到地面。但那毕竟是撒克逊施舍给他练习的武器,想收回时就收回,他使得也不那样趁手。 那天之后,撒克逊带着他第三次回到地下的武器库,这次却没朝深处走,打门口向他示意了一下墙上琳琅满目的刀具收藏,剑眉微挑,示意他可以随便挑一柄。他想对方大概是碰上了千载难逢的好心情,卸下腰间的刀,却也不明白这莫名隆重的仪式感来自何处。陋室里争奇斗艳的金属光泽搞得他头晕眼花,镶了珠宝或是雕花的更是碰也不敢碰。绕着墙角走了三圈,指中了整面墙上最不起眼的一把刀。 那刀通体漆黑,细看之下,正反面皆有两道血槽。刀柄为平直的木制缠绳,双弧形刀首,刀镡为椭圆形。刃长约七十厘米,不反灯光,却自泛着一层蓝紫色的幽光。与大部分腰刀不同,这把刀的刀身根部为直刃,自约三分之二处开始向上弯曲,刀身弧度不大,刀尖窄且略上翘,还有一段反刃。弧度凛冽优雅,一气呵成,看得出锻造之人功底深厚。 撒克逊意味不明地望了他一眼,抬手将那刀连着刀鞘一并取下,递到了他手里。尽管半年来他也稍长了几厘米,但这刀拿到手里还是有他将近一人高,提都提得有些费劲。眼看着那刀尖就要磕到地面,他本能地朝上一挑,被凌厉的破空之声惊到,在原地愣了半晌,才注意到撒克逊竟是后退了半步去避那刀锋。他举着刀,又不敢放下,不知如何是好。 凯特老爷重又走上前,从他手中抽了刀,刷刷挥砍数下,面上竟是有些满意神色。 “朝灵,”撒克逊说,“你算得上有点眼光,我也就不吝啬了。”说着,收刀入鞘,转手一并递到了他手上。“这是森染工匠的手笔。并非武器市场上那些摆摊的商人,而是我早年以私交获赠的一把。据说打造它的矿石来自极北冰原,叫什么墨绸灯——呵,这种虚无缥缈的吹鼓,谁知是真是假。不过,这独特材质的确是周遭红蓝减区没听说过的品种,我这些年来为这些收藏跑遍大江南北,还真没见过第二柄用这发光的黑石所制的武器。”说到兴头上,男人示意他抽出半截刀身,指着刀刃对他说,“看到这刃了吗?墨绸灯不反光,因此看似钝重而无杀伤力,但若是你用手去试——” 或许是真的难得兴起,撒克逊竟不避讳地抓起了他的手腕,将男孩葱白的指腹朝刃上一划。还未等皮肉入刃,食指一痛,霎时已经裂开了一条血口子。撒克逊见到血,眼底暗色更盛,嘴角诡异一提,竟是笑了。“看见了吗?连气劲都能撕裂皮肤,这刃不显山露水,却是开得极其锋利。我曾试过墨绸灯的硬度,比起刚金只强不弱。这刀啊,朝灵——大约是没有斩不断的事物的。” 说到这里,阿尔洛男人语气忽然沉了下来。 “你要成为刀,”他无头尾地说,“那么你必须成为它。” 来不及细想这句话内所包含的层层深意,撒克逊已经拂袖转身,竟是提步欲走。他捧着与自己差不多高的长刀,匆忙跟上,问出了从刚才起就萦绕在脑海里的疑问。 “先生,这刀……有名字吗。” 撒克逊听罢,头也未回,只大笑了两声。 “朝灵,”他喊,“你有名字吗!”
那日他从武器室里踏出,得了一把刀,沉甸甸地,在怀里抱得死紧,一丝也不肯松手。 ——这便了结了第一件事。
在那之后,发生的第二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是未子。 撒克逊自从那晚撂下一句“谁知道呢”,就真的再也未看她一眼。他和白桠将女孩带了回去,安置在朝歌和夜弦的住处,倒是给两人换了个名正言顺前去的理由。凯特老爷对此不闻不问,全权放手,任由他们两人每日带着饭菜出入那间二楼的闲置客房,一句话也没有提点过,像是全然不曾注意到宅子里还有这个人的存在。 他们也问过那女孩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她不回答,照撒克逊的说法唤她“未子”也不反对,于是也就这么称呼了下去。 撒克逊完全把未子当空气,反倒是让他们藏匿朝夜姐弟方便了许多,来去也不用再小心翼翼躲避凯特夫妇。只是,这样一来,朝歌和夜弦的生活里就不得不又多出一人。这新来的小孩占着半间房间,每日立在墙角睡觉,有一次还让起夜的朝歌吓得半死,以为哪里的吊死鬼来索命了。 后来她把这话说与弟弟,夜弦叹口气叫她少听麟止哥讲那些古朝灵流传的妖异志怪,结果不知怎的又传到了他耳朵里,不由得沉思起自己在他们心中究竟是个什么形象—— 因为,那故事其实是有一天夜弦在厨房帮忙,未子与她看雪时说的。 朝歌一向好奇几百千米开外的远京,时常和弟弟一起扯着他问东问西。他在那之后虽说是清闲了,直线距离从隔着两层楼变作隔着两堵墙,与姐弟俩相处的时间却并没有增加。年幼的朝灵们生活在同一座屋子里,却要依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见上一面。 说不上情愿或是不情愿,平日里能从早到晚见到的活人就这一个,不说话也得说些什么。未子不说她来自哪里,也不说他的过去。“我没法说远京,”于是那天她对朝歌道,“但我可以给你说个远京的故事。” 然后,根据受害人回忆,对方就用极好听的标准朝灵语,描述仔细,文句精致,语气毫无波澜地——讲了一个吊死鬼寻仇的故事。 这事说来好笑,细想之下却并无什么可笑之处。未子似乎很难亲近,但其实也不然,像是会一本正经板着脸讲鬼故事的类型。 他们这些住在阿尔洛城里的朝灵总是比实际年龄成熟不少。白桠自不用说,朝歌和夜弦虽足不出户,心里却都明镜似的;他与人相处上没那等天赋,但胜在对外界发生的一切都毫不在乎,我行我素,某种意义上也是大彻大悟之人的做派。 未子却又与他们都不太相同。 这个女孩在很多地方与他类似:遗世独立,不沾人间烟火,依自己的准则生活在独一人的世界里。但她又不像他。 他拿了刀,打了架,伤了人,一个人坐在院里的参天古树上头发呆。 她自从那天晚上输了一着,见撒克逊对自己视而不见,便再也没拿起过匕首。 他话不算少,很多时候闭嘴只是因为读不懂气氛,唯恐说话伤了人。若是让他一个人在房间里闷一天,就像晚秋那阵子每日与刀相伴,虽然表面上看不出区别,但的确是差点被憋出毛病来。反观未子,没人与她搭话时整日整夜一言不发,甚至几个小时或坐或站一动不动,倒像是进入了最自在的状态。 他最为恐惧的与世隔绝,她倒是甘之若饴。 未子瘦削高挑,肌肉锻炼紧实,或许是女生发育要早的缘故,身高竟比他还要高一点,两人并排在一起,他在气势上隐约就被压了一头。 他生得一张女孩子般的漂亮脸庞,眼睛又大又亮,若是单把这脸照着印到画布上,简直像是珍宝般的,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美人儿了。所幸,拜与生俱来的木楞气质所赐,朝灵男孩儿举手投足都是一板一眼,气质里半点阴柔秀气之感也无,连带着那张脸也就并不时时那样显眼。若是相处久了,很容易就会将他的美貌忽略过去。相较之下,未子一头干练的短发,只有两鬓各一缕柔顺的黑发垂下,虽说不会被认成男孩,但也并不是那种漂亮的女孩子。她的周身总缭绕着某种虚无缥缈的氛围,像是打落雪的水晶球里走出来的一般。比起分辨性别,这种独特的存在感更容易在初见时震慑到他人。 独处时,她总是负手而立,脊背挺得笔直,一双珍珠般的眸子嵌在眼窝里,薄唇抿起,乍看之下,还真会让人觉得与他有两三分相似。 “未子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吗?”有次朝歌嚼着白桠做的蛋挞,靠在床沿的枕头上问。 “我觉得不是。”他将最后一口咽了下去,手指上沾了碎屑,于是就舔了舔。“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朝歌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他的意思,前仰后合地笑起来。 “你是说,你不知道她比你大还是比你小,所以不确定她是不是妹妹?” 他顺着对方的话想下去,意识到自己的思路的确走偏了方向。“就算她确实比我小,我也……” “哥。” 他愣在了原地。 说未子,未子到。大门好巧不巧地被忽然推开,那短发的女孩站在门口。他和朝歌对视一眼,不确定对方听到了多少,彼此都稍微有些心虚。未子看了一眼两人正在消灭的甜品,又转过视线去看他。 “凡尼纳德找你。” “哦。”他从床上翻身起来,在门口与对方错身而过。“朝歌,”关门时,他听见那女孩在他身后说——“请问,我能偷一个蛋挞吗?”
于是由朝灵和一个阿尔洛少爷所组成的小家庭又多了一名成员,虽然话不多,但比他要可爱得多(朝歌语),壁炉里的火也跳得更旺了些。 ——这便了结了第二件事。
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这一切得以发生的原因。 自打那天起,他有了刀,不再跟随撒克逊练习,而是正式成为了凡尼纳德的护卫。 护卫的第一天是在病床旁进行的。 凡尼纳德其实并没有受什么重伤,只是在身上被划了几道口子,但这也足以让撒克逊·凯特暴跳如雷,命令他必须在床上静养到愈合为止了。 有几个纨绔子弟找了凡尼纳德的麻烦,这一点现在凯特府上已经人尽皆知。 这些难成气候的半吊子忌讳撒克逊和凯特家,原本并不敢真正和凯特少爷动手。然而所谓无巧不成书,其中家里新得到一个女朝灵,据说是个能打的,便提议说不如趁这机会放出去试验一下,就算真出了什么事,反正五岁的女孩子也不能玩儿,扔就扔了,算不到他们头上。 于是这件荒唐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后来那几个可怜的少爷中的一个招供说,他们当初只是叫那个女朝灵给凯特少爷“上一课”,是真没想到她竟然带了武器,想下杀招的。他就这件事问过未子,对方却摇摇头,解释说自己并没有取对方性命的打算。 “他们叫我给那个人‘上一课’,”她回忆说,“于是我就想给他上一课啊。” 谁也没有撒谎,各自说的都是真相,拼图却拼不到一块儿去。这认知上的差距究竟出在哪里,他想了几天,某日忽然如当头棒喝,竟一下就懂了。 未子所知的“上课”,恐怕与他来了时茵城之后所体验的一样—— 是汗水,鲜血,伤痕。是关节脱臼,骨头碎裂。是由痛苦和在那之上的痛苦所编制而成的,将教义铭记在骨血里而非笔记中的场景。 按照她的理解,她在某日的归途中拦住对方,想要给凡尼纳德‘上一课’。然而,对于那些养尊处优的阿尔洛少爷来说,只是一点猩红,就仿佛和平的日常悉数崩塌,要伤及性命,恐惧得无以复加。 这一点却也正救了未子一命。 那天,打墙头跃下,只是稍稍舒展筋骨,她就注意到凡尼纳德没带武器,也不像是该被教训的主(她的新主人们倒是更像坏人)。有些诧异为何会让她来对付这样一个少年,女孩却也没多想,匕首出鞘,那就是打算刀刀见红。躲在后面的阿尔洛少爷们哪见过这样淬炼纯粹的森森杀意,吓乱了阵脚,再想到捅出篓子会有怎样的后果,顾不上暴露身份,忙不迭跳出来阻止少女进一步的动作。 这下人赃俱获,撒克逊板着一张脸去交涉之时自然无人敢拦。本着必须息事宁人,不计后果也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精神,那为首的家主毫不犹豫地将“赃物”——实施暴行的朝灵女孩送了出去。“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那人说,“只求您不要难为犬子,他没玩过朝灵护卫,不知者不怪,您大人有大量……” 凯特家主不耐烦地一摆手,心下只觉得两人明明同为平辈,自己甚至没有爵位,对方却在面前如此卑躬屈膝,看着叫人厌烦。想到这里,他也不愿再多做停留,提了那个惹事的女孩便打道回府了。 他自己不需要护卫,在妻子的提点之下,也已经为儿子倾心力养了一个。珍贵的镯子寻了一对儿可以夫妇同戴,扎人的宠物买重了就教人头疼。回到家里,撒克逊已然是憋了一肚子火气:既气凡尼纳德这儿子半点凯特家战士的样子也无,出门连武器都不带,竟然被一个朝灵欺辱至此,又气那些不长眼睛的公子哥,被父母教成了什么样子;想到这里,更是气那些谄媚做作的父母,家产爵位全是伸手得来,半点真本事也没有—— 越想越气,也不顾天色已晚,就打发白桠将他叫到了庭院里。同样的款式得了两套,自然要比较一下哪一个质量更好些。所幸,他自己挑的那个还算争气,没被别人送的比下去,算是在这熊熊火气中给了他一点快慰。若是别人送的比自己选的还好,那他可能当真要怒火中烧,将这宅子的房顶掀了也不一定。 也是因为这样,他的胜利在撒克逊那里就显得更为重要,也难怪对方心情好得出乎预料。他的身上如一开始撒克逊所允诺的那样,在脊背上“刻”了凯特的家纹,伴随着通红的烙铁和铭心的剧痛,他也就真正成为了凯特家的所有物,再没有回转的余地—— 即便是死,撒克逊笑着说,也只能回来做我家的地缚灵。 之后的发展顺理成章,这三件对于凯特家并不重要,但对于他们几人来说极为重要的大事,也就随着冬日渐深,一件件发生了。 这其中,做凡尼纳德的护卫这件事情,比他们中一人想得长,却又比另一人想得要短。自那日起,他开始在凯特少爷十步以内的阴影里站着,从晨光乍现到日落西山,亦步亦趋,数小时也不敢分开。
这一站,就是十年。
◍ 春风桃李花开日·end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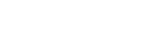










 楼主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