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尾树 于 2014-1-30 00:25 编辑
哈哈哈哈哈本章脱离了一击草稿流,我临发前还改了一遍我真是良心作者!感动你我,从拒绝大纲文开始哈哈哈哈哈哈。
月树武道馆日常之要有命(下)
初云不见了的那个下午,尾树就觉得不对劲。原因是初云竟然留了个纸条,上面写到,“我、暂时、离开”,后面还跟着一串花里胡哨的桃心。知道尾树不认识几个字,初云在下面还画了一个双马尾的自己抱着太刀“莲”往前跑的样子,在她背后画了个门,上面写着“月树”,方便他搞明白。大概是知道尾树对于师傅神雁一声不吭走了有怨气,她离开去执行少主任务前到底是吱了一声。 虽然初云大了点儿之后也经常跑出去玩儿,但尾树一直规定了门禁,绝对不能在外面过夜,所以初云都是到点儿老老实实的回来,乖顺得很,这次倒是做了个大的。 现在先是破天荒的对于“出门”这事儿留了个纸条,接着晚上到了点儿没有回武道馆。眼瞅着暮色四合,天边儿的天已经从耀眼的紫红换成了淡漠的蓝黑,家家户户都日落而息,晚饭的香味儿在一条街上四溢着又渐渐消去,烛火映上了窗,尾树开始有点儿急了。他把自己武道馆的门关上挂了锁,昏暗中,和对面始终紧闭着门的“花”酒铺沉默的隔街相对。 他拉了拉旺财,先去初云可能偷鸡摸狗、顺吃顺喝的地方绕了一圈,然后失去耐心的让放手让旺财带着跑,结果这个蠢货白吃了那么多东西,走走停停的、连远京城墙边儿都没靠上就放弃了,坐在地上瞪着无辜的眼睛看着尾树,就像它第一天被初云抱回来时一样。 “废物东西!”尾树忍不住踹了旺财一脚,旺财委屈的呜呜了两声, “麻痹财也没旺,人也找不到,养你干嘛吃的!找不到就把你炖了吃!”旺财耷拉下脑袋,失落的呜呜了两声。
尾树大半夜在街上嚎,“初云!初云你这个小崽子给我滚出来!”,被各家开窗开门的纷纷骂了一通,最后还是没找到,被半夜吵醒的好心人的建议等天亮了找找巡逻的戍卫。尾树也没辙,只好回去睡觉。 天蒙蒙亮,尾树就惊醒了,井水抹把脸,抄上剑就出去了。又兜了一大圈,最后才不甘心的逮着个看着眼熟的兴许见过的戍卫问,“最近远京有什么大事儿?” 戍卫一见尾树,惊讶的说,“你还不知道啊?最近两天有阿尔洛的人贩子来了!” 尾树一惊,刚要细问,那戍卫自个儿耷拉着肩,跟昨天晚上的旺财似的,“可是我们都没查着。”尾树这下也不知道要去哪儿能找着,一个人又坐不住,焦心的在街上像没头苍蝇似的转圈,身上的汗湿了衣服,大敞着衣襟,一层层洇透的布料有的没的黏在身上,不舒服得很。 眼瞅着要夕阳西下,尾树才抱着剑怏怏的一个人回武道馆,踹开门,除了最初门开那几声“吱嘎吱嘎”,武道馆里静的一根针掉下来都听得见。养了初云十三年,还是头一回她没在家。夕阳从背后右边斜射进来,映在武道馆大堂地上红彤彤的,和尾树黑漆漆的影子对着。在寂静中站久了,尾树觉得自己右侧的脸颊都要被夕阳烫熔化了,而身上的衣服又在汗湿过后冰凉的贴着肉,让他一阵阵发冷。 尾树转身在门槛上坐下,望着对面的街道,心里那口气始终吐不出来,憋在胸腔里,不断地膨胀。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花”酒铺仍然闭着门,门上挂着锁,锁上浮着灰,仍然一副无人打理的样子。他专注的看着,从酒旗杆的顶尖儿上,眼神慢慢往下,到两侧雕刻着有些粗糙的花叶纹的门槛,他细细的看一遍,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一样。他细细的看一遍,想象着门从里面打开了,鞠花撩着头发站在柜台边上,一手持着酒吊子,日光照在她摊开的账本上,记着尾树这周又赊了四两酒。 初云到底去哪儿了?初云是他一道天堑似的坎儿,是他半夜抹不掉的回忆,是他寄托和补偿的心肝心尖子,是他亲手养大的孩子。初云也会像鞠花这样,只出现在他的记忆中吗?又何止是鞠花——父亲、母亲、师父、师…… 他茫然的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从门槛上弹跳起来,直奔到后院去翻墙。果然师弟远清也不在! 妈的!尾树隐隐觉得这事儿性质不对了,要是初云真是不小心被阿尔洛人贩子拐走了,怎么会留条!远清虽然也经常不在去山上采个药什么的,那也没这么巧的事儿吧。 尾树的怒火一下聚集到前阵子初云认的那个义兄身上去——被自己捡回来,最后却是被戍卫带走的乌秋。混账小子!这事儿八成跟丫脱不了干系! 尾树撒丫子就冲朱雀殿跑去。他平时很少走到圣盾塔的北边去,很奇怪自己现在一边狂奔着一边还有空想:这里的石板路怎么踩起来感觉更平坦。跟乌秋有关就说明最起码现在不是生死不明的悬心,他还有空继续想点儿别的。 一路旋风似的刮到朱雀殿,尾树先是被拦了下来,正在他烦着要怎么解释,要不要干脆横冲直撞进去时,接着又被放进去,好好的给带到了。这一折腾,尾树那一股子攻心急怒搅黄了一半,见到了乌秋,本来想拔剑砍一通的,变成了挥拳就要打,乌秋倒是三跳两跳的就躲开了,放低了声音喊着,“等等啊,哎,哎,袍子别踩着了,新做的!哎哟我说初云好好的呢,君子动口……”他想到尾树估计也听不懂“……总之别动手啊,初云有人保护着呢你放一百个心!哎,黑鹫你站远点儿!” 尾树听了这话停了手,面色不善的攥着乌秋的手腕,“果然跟你有关系,到底怎么回事儿?!” 乌秋挣了挣,抽了手回来,背着手撑大个儿,清了清喉咙,“事情啊,不是你想的那样。” 尾树斜着眼看他,“我想的哪样?” 乌秋撇着嘴不说话。尾树往前迈了一步,接着问,“你说初云有人保护着呢,那她是干嘛去了?” 乌秋靠着柱子望着天,“反正保护她的人个个身手不比你差。” “滚你妈蛋!” 乌秋在心里叹口气,头疼想果然怎么也避不开这一关,这才正了脸转过来对尾树,“初云吧,是小孩子心性,喜欢热闹,就让远清带她出去玩了玩……” “放屁!” “那……”乌秋斟酌了一下用词,“那换成这样:初云想见见世面,尝尝时茵的瑰丽酒,所以就和新朋友一起出去了,新朋友们都很友好又……” “放你娘的屁!” 乌秋跟着又换了套说法,“初云跟我说想去找神雁,哎呀我本来不同意结果她软磨硬泡……” “放你娘的狗屁!找他不跟我商量?!” 乌秋已经姿势都不带换的张口就来了,“……初云怕你把她给吃干抹净了就拜托我救她出去!” “放你娘的狗臭屁!” “……初云和我玩儿躲猫猫,我倒数了十下,她人就已经在路上了!”接下来乌秋又换了七八种说法,尾树话都懒得接,瞪着乌秋,乌秋也嘴皮子磨烦了,一屁股坐亭子里,“你说吧,我怎么解释你信?” 啰嗦这半天,尾树也知道乌秋说不了实话,“你知道她现在处于什么状况?” 乌秋一看情况有好转,好话说尽了,指天画地、拍着胸膛、信誓旦旦的再三保证了初云的安全,这才把尾树哄回去。眼瞅着那个整个人都乱七八糟剑却抱得很紧的男人不甘心的出了去,乌秋心里刚舒了口气,转头又想到派出去的人,心里暗暗想着他们在外面的情况,向女神祈祷了三秒,盼着行动顺利大家早日回来。只可惜往往天不遂人愿,后来乌秋也头疼的想过,是不是如果不派初云出去,就没有接下来纷乱跑偏的事儿,但这世上的规矩简单得很:没有如果。
————————————————————这里是隐藏的(下中下)————————————————————
远清风尘仆仆的赶回自己宅院时,已经觉得要精疲力尽了。
从阿尔洛城市星夜兼程回来过红区的路上,他们还遭遇了魔物,打下来之后自己和几个同伴都负了伤。于是,当远远看到远京修了一半的城墙和一排排熟悉的房屋顶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互相笑着拍拍肩。 “可算到家了。”远清说了一句,旁边的夜霾不出声的点下头,也看向他所看的那一片冒着炊烟的房屋顶。远清又想到没回来的那一个人,心里又纠结起来,要说,怎么说?他在心里长叹口气,“走吧。” 先是夜间向乌秋汇报,跟着是第二天应付问询,他们个个一副历经千难万险堪堪逃出来的样子,脸上的表情又疲惫又惊慌。除了表情不大对,历经千难万险倒没说错。又折腾了一上午,远清饿着肚子下午才回到自己宅院,还想着绕一下从后门进去,以避开可能在前门蹲等的尾树,进了家门就发现尾树一脸菜色的、弯腰驼背的翘着二郎腿坐在他家墙头上打哈欠。他看见远清到,愣了一下,眼睛一亮,整个人都生动起来,隔空指着远清鼻子,冲他中气十足的大喊着,“你小子给我等着,我看完初云就来教训你”,跟着利索的扭身跳回自己后院,奔着去找初云。 远清眼神一暗,他觉得自己这一路叹气已经叹得太多了。正回屋子里放了东西、换了衣服,要打水烧水时,夜霾如约来找他拿草药,敷一敷刚才跟魔物打斗时受的外伤。 远清给夜霾大略的检查了一下,“你等等,我现在去给你找药。” 夜霾刚应了一声,就警戒的站起来,神色不善的面对从对面墙上跳下来的男人。后者直接略过他,毫不客气的攥住远清的衣领往上提,“初云呢?!” 这就是尾树啊……夜霾想,升起了一点难得的同情,尽管如此他还是保持着警惕的状态,随时打算插手。 远清又在心里叹口气,摁住尾树的手腕,“师兄,你听我说……初云她……”他看见尾树瞪着眼珠几乎要撑裂眼眶,表情焦急又恓惶,忽然什么都说不出口了,远清神色黯然,微低下头去、不忍心看对方,“她……初云……” 尾树看这样子也猜到什么,表情登时十分复杂,最后全聚成怒气,跟着硬邦邦的拳头就挥过来正打在远清下巴上,他猝不及防挨了一拳,脸被打得偏过去,立马就红肿起来,嘴角也破了。跟着第二下就被旁边的夜霾拉住了,拳头没一鼓作气下去力,尾树一甩胳膊,也不管这里了,狂奔了出去。 远清冲夜霾无力的摆了摆手,示意后者跟着进屋。不知道是第几次在心里叹气了,远清试图仍旧保持平时微微笑着说话的状态,拉动了嘴角的伤,有点儿小疼,“这下我们俩都需要上药了”,他对夜霾耸耸肩,转身就看到挂在那里晾给初云来偷的肉肠,忍不住苦笑了一下。初云,你究竟去了哪里?
尾树马不停蹄的赶到朱雀殿,却被告知少主不在。他对乌秋的一口怒气泄不出去,狠狠一拳打在墙上疼半天,又想到初云,感觉胸口直接冷了下去。门口的戍卫好奇的看着这个两次试图闯殿的男人突然一下肩也塌了下去,表情也变了,从燃烧的火焰变成了灰,没了型失魂落魄的往回走。 也是,初云没了,究竟逮着谁发气又有什么意思,尾树混沌的想,又一个初云没了。一时间,他思绪纷乱,想到当初说了阿尔洛那地方不好混怎么初云还要去,要是初云在这儿马上给她屁股上来两下让丫长教训,可是初云没了……想到初云和鞠花一样都消失在了外面,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在不知情的处境下,就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要去的地方、要做的事,而……又后悔与其这样,怎么没有当初干脆再一次杀死初云,也好过现在。所有混乱的想法最后都变成嘴边呆滞的重复:初云死了……十三年后,又死了。 同样的橙红的夕阳,照着他前方的行路,像初云刚第一天不见了他奔去找不到、回来时那样。简直是复刻的黄昏,笼着更加绝望的人。尾树觉得自己一颗心像放到油锅里炸过一样,冒着焦灼的小泡,又一个个破灭,渐渐变成冷硬紧缩的一团死物。 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遇到这种事? 尾树行尸走肉一样晃回武道馆,树桩似的立了一半晌才咬牙推开武道馆的大门,却看到乌秋贴在大堂墙壁上罚站。他怒气翻滚了两下,还是没忍住又噌的窜上来,“要他妈不是你……!” 他抬脚就踹向乌秋,跟着噼啪一阵乱打,毫无章法。乌秋自知理亏,硬着脖子挨揍,把头护住了,一边心里觉得十分对不起初云和尾树,一边惦记着别打着脸,回去没法儿交代。尾树一开始用了劲儿,后来打着打着觉得没意思,喘着粗气住了手。看着躺在地上的少年,想起几年前、三个人在后院儿里种丝瓜种葫芦的事儿,那时候初云才六七岁,整天捏泥巴,都抬不动一把金属制的剑;乌秋也很快学了武道馆特有的死皮赖脸、满口跑火车的样儿,歪歪扭扭的举着竹刀;尾树抄着手、叼着叶茎,看着他们俩没心没肺的大笑。而如今是怎么一回事儿?武道馆为什么空荡荡的只剩下了自己?为什么初云消失在外面?他又为什么在打这个少年?尾树觉得糊涂了,是不是做梦?地上的乌秋瞅着他的脸色爬起来,咳了一声。 怒气泄下去了,凄凉跟着浮上来。尾树忍不住干嚎起来,乌秋从没见过他像这样拳头用劲抵住脑袋、仰着头野兽一样从喉咙嚎出没有意义的声响。他忽然抬起胳膊,举高手里的剑用力掷远,砸到墙上“嘭”的一声巨响,剑脱离了鞘分着“哐”“哐”重重的掉下来,好大一个动静。 那剑就从乌秋脑袋边儿飞过去的,带的那阵风让他许久以后都觉得这侧的脸颊冰凉。而他此时看了看背后摔在地上分离的剑鞘,剑在阴影中隐约有凉光,他又转回头看了看眼前的尾树,一时不知道要说什么。他挪到颓丧的尾树面前,默默的坐下,跟他平齐,视线越过尾树落到街对面的闭着门、积着灰的“花”酒馆上,他又收回了视线,盯着眼前的一小块地方。 两个人对着坐了很久,一言未发。天已经暗了,街上仍然是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节奏——各家饭香四溢又飘远,再点起了蜡烛,一日的开张敞亮都收成了屋里的悉悉索索,仿佛对人走人留都无动于衷,少了谁都一样能把尘世原封不动的继续下去。武道馆大堂地面上映着的,从殷虹的夕阳光景变成了晦暗朦胧的夜色,地上也冰凉了下来。 最后还是乌秋先开了口,话在他胸膛里、喉咙里、舌尖转了不知道多少回,最后还是,“对不起。”尾树沉默了许久,摇了摇头。 乌秋低着头接着说,“我会把初云找回来的。” 尾树张嘴呆了一半晌,才猛地一抬头,劈声厉喝,“找回来?!初云没有死?!” 乌秋也张大了嘴,“啊?”他猛地意识到尾树是误会了,连忙摆手,迭声道,“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又觉得话说得太早,立马改口,“现在的消息是初云失去了联络,我们没了她的行踪,并不一定……就……就死了。” 尾树咧开嘴,先是无声的笑开了,猛地拍了一下乌秋,然后彻底哈哈大笑起来,“我真蠢,自己吓唬自己!没有死,还没有死!”他简直笑个不停,乌秋看着他一瞬放晴的表情开始怀疑刚才那顿是不是白挨了,如果一开始就告诉他初云不是死、只是失踪了的话……结果只是闹了一场乌龙!也并不算是乌龙,乌秋放松了没一秒又紧跟着一颗心再沉下去,到底初云还是失踪了,一个十三四岁的朝灵女孩失踪在阿尔洛人的地方,并不比失踪在红区的森林边缘的鞠花强多少。而尾树还不管不顾、时断时续的笑着,和刚才像放馊掉的蔫塌塌的腌萝卜样儿不同,他此刻和刚爆炒出来的腰花一样充满了生鲜活泼的气息。 初云已经出事儿了,尾树可不能再出问题。乌秋看着慢慢笑停、又显出往日气势的尾树,多少还算欣慰,挑着用词、斟酌着开了口,“我们接下来可能出去找初云,你跟我们一起行动肯定能更快找到她。” 尾树恢复了之前的德行,一脸“你小子欠操就直说”的表情,眯着眼看过来,“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吗?你向我保证初云很安全才是多久前的事儿?”乌秋说不出话来。尾树活动活动手脚,站起来走到墙边,弯腰捡起剑和鞘,看了一看,“哐”的一下收到一起、紧紧攥住,“我会把初云带回来,用不着别人。” 乌秋觉得,在暗沉沉、空荡荡的武道馆大厅里,这话听起来更像是一种驱赶。夜间的冷风吹进来,乌秋忍不住拢了拢身上的衣服,不小心碰到了挨揍挨得很的地方,疼得嘶一声。尾树听到了,握了下拳,什么也没说,拿着剑转身就上楼了。
乌秋走的时候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月树武道馆的招牌,只有一个钉子固定着一角,招牌歪下来。他知道如果碰到风大的时候,吹着它会晃,这是有那么几个下午,他像武道馆里人似的坐在门槛上看着街道发呆时发现的。他又凝眸注视了一会儿“花”酒馆的酒旗,酒旗凄惶的在夜风中飘着,门依旧紧闭,仿佛从来没打开过一样,从没有人站在这里笑意盈盈的举起手中的花生米和米酒一样。很久没有到这里来了,乌秋感觉这里既熟悉又陌生,而如今,仿佛陌生还多一些,毕竟有些人走掉了,让这里变了太多。他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这里,乃至这片土地,是他的责任。并不是因为这里住着那些他熟悉的人,而是为了即使大家都不在了,也要有人继承某种意志,如生生不息。 初云是我的错吗?乌秋想,也是,也不是。但这世上的事情又有几件能以对错区分,不管怎么说,他的担子都背负定了。黑鹫向他报隔壁远清准备好了药酒,乌秋点了点头,“取了回去吧”。 这条回去的路,也很久没走了。乌秋步速均匀的走着,忽然才明白神雁曾说过的关于尾树的另外一句话,意志才是最大的天赋。跟着那个简直油盐不进的神人难得的叹气摇摇头,“可惜未悟”。 他想着竟是我先明白了,恍了下神,猛的眨眨眼,深吸了口气,沐着月色,加快了脚步向朱雀殿走去。
这时代潮涌澜翻,生离死别不由人。
——完——应该是月树武道馆日常系列都完了吧——已经没有日常可以写了啊混蛋——武道馆没了女主人凄凉的一逼有啥可写的——
等等神雁是这么说的吧?我都忘了我前面怎么写的丫的话了23333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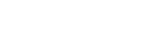










 发表于 2014-1-29 08:07:55
发表于 2014-1-29 08:07:55






 楼主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