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409.12-410.5
◍ 廿贰 ◍
时茵下了一冬的雪,大雪封路。
二十二、十轮霜影转庭梧
听凡尼纳德说,有的飞空艇航班都因此而不得已而取消。凯特家主原本似乎也有计划,因此被耽搁了,干脆就留下来与他和白桠一起过了新年。尽管饭桌上心思各异,氛围也因为话题的缺失而显得有些尴尬,但凡尼纳德总还是挑了些生意场和联谊上的趣事来说,三人默契地做一做笑脸,总也没有冷到外面的气温。
伴随着槲寄生和蜡烛彩灯以及新鲜花束,光芒暖融融地,这个凯特家的新年在这么几年里面,倒真是算得上温馨的一个了。 冬天终于过去,早春的第一缕金色阳光窜入庭院,是万物复苏,气温回暖的好时节。那天他出去活动筋骨,眨眨眼,猛然意识到自己连天上有没有云彩都看不清了。一个冬天都阴阴沉沉的,现在天空骤然开朗,光线刺得他有些想流泪,走路都不自觉地朝阴影里靠。 他没说,但凡尼纳德显然是注意到了。凯特家主让他去看医生,他答应了,但没去,空出的时间全用来在时茵城里晃荡。眼睛不好了,能记住的东西就要多记住一些,他在这方面也确实豁达。 时茵是花都,城里除了缤纷的花朵就是林立的树木。他曾经在树林里与未子比试过,现在他就在那些树顶上躺着。有的时候一躺就是大半天,但他现在很少在外面睡着了,更不会像曾经一样从枝头上掉下来。凡尼纳德后来应该也是知道了他做的事情,虽然懒得评价,但也确实不再提起眼睛的事情了。 他们还是吵架。其实严格来说并不算吵架,只是他单方面地站着,凡尼纳德发泄他骤然而起的怒火。事实上,他觉得这个状态非常不对,但朝灵少年有限的人生经历实在无法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别的选择。他不敢也不会尝试去顶撞对方,就只能像个木桩似的站着,但显然——这也不是正确的应对方式。 然而,就算是这样,他依旧没有起过离开的心思。很快,他就要过完在凯特家的第十一个年头了。这座不算旧的大房子承载了他最后的童年和少年,就像白桠看着凡尼纳德从小长大,成为现在的样子—— 他遇到的人们也看着他跌跌撞撞活到现在,仍没完全通人性,但至少活成了一个人样。 春风拂过,野玫瑰次第开放,他在时茵经历的第十一个春天与他经历的第一个同样盛大。细细数来,这十一年间发生的事情,大的小的,许多都发生在明媚美好的春天。 时茵的四季分明,景色大好,但他还是最喜欢春天。春天有鸟鸣,有花香,有争相生长的万物,也有好闻的泥土气息。春天有樱花开放,有少年少女的诞生之日,有夜晚舒爽的凉风,也有从远京一路跋涉而来的人贩子。
就连这个故事的结局,也还是发生在春天。
五月底,他一时兴起,大白天从集市里穿过,想听些嘈杂的人群喧闹,给自己衣摆稍微沾些生气。从一个房顶跃到另一个房顶,他蹲在房梁上,正准备转身,却忽然在下方扫到了一大片的黑色。 时茵极少有黑色,这一片黑就显得格外刺目。尽管远京的建立已经是二十几年的过去式,时茵外来人口增加,对朝灵的反感也没当初那样强烈,但朝灵的人口比例还是极少。 他趴在屋檐上,想要尽力看得清楚些,无奈一片黑色的后脑勺混成了一片黑色的海,无论是朝灵还是贩卖者都糊作一团。盯的太久,眼睛有些酸胀,他揉了揉,再睁开时,猛然撞进了一道闪光。 是一柄剑。 明明世界都是模糊的,那柄剑却清晰得过分。过了十一年,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还记得那柄剑的模样,从柄到剑身的线条,描摹而下,分毫不差。 那一瞬间,他的眼睛里除了那柄甚至没什么特色的刚金长剑,以及握剑的阿尔洛人,竟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他的手握上了刀柄,用力大到直接发白,整个人都崩得死紧。 这是从未料想过的重逢。像是被长鞭击中,伤口火辣辣地痛,神志却是从未有过的清醒。十六岁的朝灵少年轻轻摸过自己刀柄上的绑带,无声地与自己交谈。 要去么。 要。 那之后呢。 不管。 凡尼纳德呢。 对不起了。 想到这里,他抽刀纵身—— 刚要从房顶跃下,却又在其中一个朝灵走到檐下的时候猛然止住了脚步,半截乌黑刀身已经出鞘,被他拿手按着,硬是一寸一寸地送了回去。
那是一个红衣服的少女。
她的头发打理得很漂亮,衣服也很整齐,明显不是像他们那时刚刚长途跋涉而来的样子。他蹲在房檐上,抱着刀,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形象可疑,只是死死地盯着她的脸,眼睛眯了又眯,想要确认自己的猜测。 与此同时,一个带着贝雷帽的白色卷发少女走了上来。她比红衣朝灵要略矮一些,步子迈得很小,却自有一种优雅。尽管他看不清衣着的细节,但隐隐也觉得花纹精致,装饰层层叠叠,不像是普通市民穿的衣服。红衣的少女歪了歪头,整理自己的盘发,在黑色的海洋中,只有这一点红色分外耀眼。两人走到一起,但似乎因为语言不通而没有发生过多的交谈。他还想再看清楚一点,无奈眼睛实在酸的厉害,眼泪都要涌出来,只能埋头闭眼稍坐休息。 将生理性的泪水憋回去,再睁开眼睛的时候,那两位少女已经牵上了手,绕开朝灵和阿尔洛组成的人群,朝集市中心走去了。走出几步,红衣的少女忽然转头,望向了他的方向。尽管只是一瞬间的四目相对,但他几乎差点失了半辈子把持稳重的淡定。少女似乎有些疑惑,别过头,同身旁的阿尔洛少女一起,渐行渐远了。
——不会错的,是花浅。
他闭上眼睛,忽然就不想再依赖这没用的器官。 这世界上,能把红衣穿的像她那样好看的人,他还没见过第二个。 朝灵少年忽然就想起了自己打碎朝歌的蝴蝶头饰那天凡尼纳德的眼神。这或许就是自己将对方的心思全数摔进纷纭境与浓艳场的报应吧,他没由来地寻思,现在要从这其中勘过的人,换做我自己了。 但其实,他并说不出来自己究竟是什么感受。恍然间拿自己与凡尼纳德做了比较,细想之下却也不是这个道理。 想不出来,他在原地蹲了半晌,蹲到膝盖发麻,起身,朝平日躺惯了的树林里去了。
那天,他在树林里一直坐到太阳落山。回凯特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他按照平时的习惯打墙头翻过去,刚落地,额头却忽然落了一记重击。隐约看见对方价值不菲的皮靴子横在眼前,又是毫不留情的一下,他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昏了过去。 再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躺在了地牢里。 上一次进来这里,还是凡尼纳德为了朝歌出手伤人的时候。虽然想起来觉得不远,但扳手指一数,才发现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自从撒克逊离家,凡尼纳德正式成为家主,他就几乎没有受过刑罚(对方那些激动的时刻并不会真正对他造成什么伤口,他也不觉得那算是某种惩罚或是屈辱),这一天来接连发生的事情有点多,多得让他头晕。 回想一下的话,那双鞋子应该是撒克逊·凯特的。不是因为他认识对方的鞋,而是因为那人的儿子鞋码没有父亲那样大,这样结实有力,丝毫不拖泥带水的重击,也的确像是对方的风格。 比起掐住自己脖子又松开的凡尼纳德,他想,撒克逊先生做起事情来,要有效率多了。 等了一阵子,地牢外一点声音也没有。不知道自己会被关多久,又一天没有吃饭,本着节约体力照顾消化系统的原则,他在墙角找了个姿势躺下来,就这么开始了睡眠。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那门再一次被打开的时候,面前出现的是一身戾气的凡尼纳德。灰发的英俊青年眼下一片青黑,眉头蹙得死紧,端着烛台,连蜡就要滴到手上了都没注意。他本想提醒对方,一开口才发现嗓子干得要冒烟,几乎发不出像样的声音。凡尼纳德好容易分出点心力关心他想要说什么,正巧一滴滚烫的蜡滴落在他指节上,疼得凯特家主猛然缩回拇指,眉头就更是拧做一团。 他没说什么,径自和对方出了地牢,朝楼上走去了。 两人一路无话,直到走到门口,凡尼纳德推开门,中庭的光线洒进楼梯口,他才用嘶哑的嗓子问出了声。 “凡尼纳德,“他问,”先生有没有因为这事……” 问到一半,却又不敢问了。他想这太不像自己,搜肠刮肚,却愣是找不到一个能用的措辞。听到这个问题,凡尼纳德顿了一下,却又立刻像没事人一样,径自往前走。“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他轻轻说。 “有。”他回答,“这是因我而起的,如果真的有,那么我应该受责——” “责罚,责罚,责罚!”凡尼纳德转过身,厉声打断他,“你就那么想‘受责罚’么?受我的责罚!” 他不知道如何回答,跟着对方站住脚步,却很明显被理解为了某种程度的默认。凯特家主又就这这个话题质问了他几句,他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但显然只达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灰发的青年摔了烛台,揪住他的领子,他被对方猛然爆发的气势压退了两步,垂下眼睛,犹豫了一下,说出了一直以来都想说,却又从未找到机会的话—— “事情不该变成这样的,凡尼纳德……我可以解决现状么。” “你想解决?”灰发的青年忽然就笑了,“你真的想解决,我告诉你怎么解决——”他松开手,朝门口一指。“你出去,别回来,这样一来,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解决。” “这不是你的真心——” 凡尼纳德再次冲上来压住他。 “你说什么?”那青年问,“你再说一遍?” “我说,”他努力地放松嗓子,“这不像是你的真心话,凡尼纳德,我以为我们至少可以——” 这话显然是说错了。滔天大错。在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自己已经被凡尼纳德揪着领子一路推到了凯特家的院门口。这期间他们还在继续交换争执,他坚持想要凡尼纳德理智一点并思考一个解决办法,而对方显然认为他的出发点放在此刻根本站不住脚(事实上似乎也确实如此)。他从来没见过那灰发的青年发那样大的火,凯特家主完全不顾形象地攻击自己的朝灵护卫,像是要将全世界的罪孽一并揽到他头上似的。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凡尼纳德将他推到院门上,那厚重的门板“轰隆”一声,竟然被撞开了一条口子。他脑袋里一阵嗡鸣,眼睛失明了几秒,耳边凯特家主的声音却更加清晰了。 “是你生病,”凡尼纳德说,“是你生病,所以父亲才会发现朝歌和夜弦,所以他们不得不离开。是你没有看住朝歌,她才会跑丢,才会听到那样不堪入耳的言辞。是你摔碎了朝歌的头饰——女神——那是我们和他们仅有的记忆了啊,而你就这样把它摔碎了?!你瞒着我们跟未子来往,然后把淬毒的刀带进家里——天知道,如果其他人,如果那两个孩子要碰到了它会发生什么!事到如今,你还有脸说,你为凯特家做过什么?” 凯特少爷猛地松开手,每个字都说得咬牙切齿,不知道是说给他还是说给自己听。“你就算是——就算是我的护卫,这么多年来,我唯一一次在外面受伤的时候,你在哪里?现在你告诉我你要解决这个现状,你知道吗麟止,你知道吗——你就是造成现状的原因啊!!!” 他这次是真的愣住了。半晌,憋出一句—— “……你当真有那么恨我?” 于是凯特少爷对他笑了,承认了这是命令,然后吼了他,让他滚。最后的细节他是一点也记不清了,满脑子都是自己做过的事情,一件一件被凡尼纳德细数出来,连自己都不愿细想的事实,赤裸裸地摆在面前。他脑海里又响起了未子的声音,时过境迁,只有女孩的嗓音干净如初—— “你会害了自己,也会害了这里的所有人。” 她说的没错,他想,她是对的,而我一开始就应该相信她的。 他按上腰间的刀,朝门外走去。时茵的街市是一如既往的喧闹欢腾,于全世界的歌舞升平之中,只有凯特家的院子里是安静的,孤独的,投石入井,仿佛入了无底洞,再也听不见水花溅起的声音。 十六岁的朝灵少年走进了盛世的繁华之中,车水马龙在身后合拢,然后将门那边的凡尼纳德一个人留了下来。 这么多年,那青年的母亲走了,父亲走了,爱的朝歌和夜弦走了,未能建立关系的未子也走了,直到现在,他在这个家里住了十一年,然后他也要走了。 最后的最后,留在凡尼纳德·凯特身边的,也只有看着他从小团子长成如今的青年模样的,白桠一个人而已。
他一步步地走在街道上,越走越快,最后奔跑起来。 黑发的朝灵少年从矮墙跃上房顶,在屋檐间奔跑,任由身后长长的细辫随风扬起。他跑过了大半个时茵,任由汗水湿透了里外衣衫,然后在听到兵刃相击声的瞬间停了下来。 他听到剑的声音,听到箭矢的声音,听到刀的声音;他听到青年的叫骂声,也听到青年的嘲笑声,隐隐约约听到几个词组,“理魔法”,“频率”,“废物”,还有——
“410年了,光会耍剑有什么用?普通人一个,连骑士校都进不去,也好意思回时茵?乖乖滚回去做你的花架子大少爷——”
他是个很简单的人。 他听到了剑的声音。 于是他翻过屋顶,跳了下去。衣摆掀在空中,像是鸟儿于空中张开了双翼。他拔出刀,听到围攻的其中一人惊呼为什么自己的魔力提取不出来了,然后闭上眼睛,挟着那蓝紫幽光迎头落刃。
听说你喜欢喝血啊—— 他在心里对手中的雁翎刀说。 亏了你十年,就一次喝个够吧!
◍ TBC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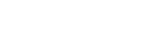










 楼主
楼主


 发表于 2017-12-31 21:17:16
发表于 2017-12-31 21:1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