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伊斯雷 于 2013-3-18 20:26 编辑
VIII
早在童蒙时,伊斯雷就在历史课本上读到过杰克·阿尔卡纳这个名字:森染曾经的执政官,恶魔之仆、塔菲血宴的始作俑者,十几年前,他的倒行逆施造成整个塔菲骑士团覆灭和数以万计平民的死亡。——家庭教师并未对此多加讲解。这寥寥数行文字就是关于杰克其人的全部,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整个苍犀馆没有一个人提起过这个名字,大家似乎都在刻意将他遗忘,上至家主,下至门房。这种统一的缄默坚韧如网深沉如渊将伊斯雷卷入其中,令他无从发问,只能将疑惑深埋心底。 他第一次真正听到这个名字,是数年之后自格尔希因的口中。在第一皇子于苍犀馆盘桓的那段时间里,两个不到十岁的小男孩经常模仿父辈煞有介事地谈古论今,其实就是互相炫耀自己那不过寥寥数年的课堂知识。一次,格尔希因说:“论起你们阿尔卡纳家的名人,‘血宴’杰克应该也算一个吧!” 那个名字在伊斯雷的耳中炸开了。过了半天,他才讷讷地问,杰克·阿尔卡纳到底是谁。 格尔希因大睁着蓝晶晶的眼睛,惊讶地望着他: “他不是你的堂叔吗?是威鲁尔伯父大义灭亲……” 这次是什么东西在伊斯雷的脑中炸开了。格尔希因开始还在为难倒对手而雀跃,但随即发现伊斯雷脸色青白,额头满是冷汗。他担心地摇着伊斯雷的胳膊,但是伊斯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天晚上,伊斯雷冒着被责罚的危险,鼓起勇气走进父亲的书房,向他提问关于杰克堂叔的事。 父亲对此似乎并不意外——他甚至不算严厉。但是他并没有给出答案。 “等你再长大一些,能够理解这一切的时候,我会把事情原委告诉你的。”他看着伊斯雷稚气未脱、不无畏惧,但已经坚毅的眼睛,轻轻拍了下他的肩膀。威鲁尔·阿尔卡纳从不抚摸儿子的头,像大多数父亲常以示亲的那样——他承认儿子还需成长,但自最初就以成人的方式,像对待一名骑士一样对待他。 然而父亲没能看到自己长大。仅仅一年之后,在那个深冬的雪夜,秘仪族长连同温斯特家族的一切在烈焰中焚烧殆尽。灰白色的余烬混杂雪花飘散在浩渺的无尽之海上,一去无踪。巨大惊恸将伊斯雷整个人冲刷成一片空白,冥冥之中,他隐约感到某种意志的存在。 多年之后的现在,伊斯雷确信那意志的确存在——跪在弥留母亲的病榻前,接过亡父遗剑“涅磐”的同时,他也接过了秘仪家族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的一切真相,尽管那未名的意志并非宿命。 生有高绝卑微,而每个死亡皆有意义。 父亲如此,“血宴”杰克也如此。
“这是维·库尔茨指明让梅辛转交给咱们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利亚姆说,声音微微干涩,“他是咱们的堂兄——躺在地下室的那个也是。” 伊斯雷皱眉。就任族长之后,他曾经问及“血宴”杰克的身后之事。杰克·阿尔卡纳虽是海德里恩和威鲁尔的堂弟,但早早就结婚生子,娶的是相恋多年的一名本地富商之女。在他被当作塔菲血宴的祸首处决之后,年轻的遗孀不愿自己和年幼的双胞胎背负恶魔眷属的骂名,拒绝阿尔卡纳家的安排,母子三人一同离开了苍犀馆。 “堂叔母当年不是回了娘家?我记得是姓……巴伦卡?”伊斯雷努力回忆了一下,“巴伦卡家也算有几分资产,她的儿子怎么会落到当矿上技师和小文员的地步?而且父亲当时就吩咐每年都给他们送去一笔很大的年金……” “叔父这份善心,算是白糟蹋了。”利亚姆叹道:“回是回去了,巴伦卡家也没给落难的孤儿寡母好脸色看。堂叔母忍耐几年,还是带着两个儿子改嫁了——当然选不到什么像样的丈夫,也没多少陪嫁,草草嫁了个三代没落的小男爵——他的姓氏就是库尔茨。至于你给的年金……有人白送上门,老巴伦卡自然乐得拿着,要是告诉你他们母子不在了,岂不是断了这一份飞来横财?” 伊斯雷哑然半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瞪着眼睛说。 “女神在上……”利亚姆作势晕厥,“别说杰克堂叔出事那么远,就连堂叔母改嫁那年,我也还在排队投胎呢……你专门过问这件事,你都不知道,我一个看热闹的怎么知道?——我是今天中午仔细调查维·库尔茨才知道的!” 伊斯雷挠了挠头。“你说得对……抱歉,利亚姆。”他低头道。 利亚姆微笑着,伸手拍了拍他的头。 “维奥雷尔·库尔茨坚持要见他哥哥的尸首,还要和你谈。你打算怎么办?” 伊斯雷沉吟了一下。“那么就把他送到总部来吧。”一直扣在市政厅不成办法。既然对方已经亮出底牌,那就在傍晚前速战速决。 “好,我派人把他送来。”利亚姆看了看屋角的座钟,两手一拍膝盖站起身来,“我得走了,两点半之前要到场。——我尽量也速战速决,完事后直接回到这儿来。” “说起来……你是去做什么?”伊斯雷打量着他精心梳理、一丝不乱的发型。 “图恩大圣堂重修的落成仪式,非得叫我去致词……不然谁穿这玩意儿?”利亚姆把下巴在高耸的绣金硬领上艰难地转动了一下,拍拍自己的肚子,“替我多谢卡梅菈的三明治——不然可怜的主教司祭们就得听它唱安魂曲了。”
IX
下午两点四十分,维奥雷尔·库尔茨被送抵骑士团总部。前来迎接的是团长副官卢佩恩。维·库尔茨之前的狂躁一现即逝——他又恢复了之前那麻木寡言的样子,对一切漠然处之,只有在见到卢佩恩时,他低声说: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卢佩恩无言以对。他那在苍犀馆担任执事的父亲每年往巴伦卡宅送一次年金,某次回来曾说起在院中见到一对四五岁的双胞胎,穿着大而敝旧的衣服,苍白纤细仿佛两根豆芽。可怜,可怜啊,那明明是秘仪的金枝……他深吸一口气驱散耳畔父亲陈年的喟叹,向这个落魄寒酸的文员行礼致意: “请随我来吧。团长阁下在等着您。”
楼梯笔直下沉,深入地底,经过不太长的石头甬道,尽头是一扇半开的苍白厚重的石门,即便大门两侧火炬高燃,仍驱不散其中逸出的森冷气息。这处地下石室是骑士团的停尸处。战死的骑士们在入葬前会先被带到这里来确定死因,然后整理修饰遗容。不过此时,室内只陈列着一大一小两具并非骑士的尸体,并排放在一张较大的石床上。 听到副官的通报,负手站在石床前的年轻男子转过身来。 维奥雷尔·库尔茨和伊斯雷·阿尔卡纳默然对视了很久。虽然并未有所期待,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与对方简直没有任何一丝的相似。——伊斯雷与利亚姆的容貌、年龄和性情也都截然不同,但他们毫无疑问有着共同的风骨,而维奥莱尔……作为一个三十一岁的男人,他的鬓角尚未花白,肌肉也未松弛,但他的眉角、前额,以及下垂的肩膀和微偻的脊背,都在在显示出摧折的痕迹。 他们双双省略了初次见面的寒暄,仅点头致意,因为不确定互相要如何称呼。伊斯雷拿出那只漆盒,向维奥雷尔递过去,但对方并没有要接的意思。 “我已经不需要这个了。”维奥雷尔看着伊斯雷,阴郁地说。 伊斯雷并没有特别的表示,只是点了点头。“那么,就由我来保存。”他说,把漆盒收回衣袋中,指向陈尸的石床:“请吧。” 维奥雷尔走上前去。他俯下身,将手放在兄长冰冷、僵硬的额头上,长时间端详着那与自己一无二致的青灰色面庞。他的脸上仍然一无表情,只有蜡烛的光在他嘴边投下抖动的阴影。良久,他转向死者胸前因瞬间高温灼热而边缘炭化的无血无肉的空洞。 “……果然是你们杀了他。”他转向伊斯雷,嘶哑声音中带了三份恨意:“告诉我,凶手到底是谁?” 伊斯雷对此并予以未回答。维奥雷尔盯了他一会儿,转回头,注意到石床另一端较小的那具尸体。 “……这是什么?” “隼鬼来袭前夜,莱维·库尔茨偷偷埋在矿场入口的东西——具体情况梅辛先生已经向您说明过了。”伊斯雷说,“既然您想要看,那么我觉得应该尽量让您看全。如果这里已经可以告一段落,就请您跟我到下一个地方去吧。”
回到地面,伊斯雷领着维奥雷尔·库尔茨阔步穿过骑士团总部穹顶高挑的淡绿色花岗岩大厅,一面向沿途驻足敬礼的骑士逐一还礼,步速却并没放慢半分。他们穿过大厅西南角延伸至中庭的走廊,来到一处独立的两层小楼,并没进入正门,而是从侧面的楼梯直接拐上二楼。推门进去是一间办公室模样的房间,放着七八张办公桌,沿着一侧墙壁还设有两张床铺。房门对侧并非墙壁,而是一带石头围栏,围栏以外便是一楼直上的挑空。一名身穿白色长袍、佩戴着骑士团徽章的男人迎上来,向伊斯雷行了个标准的骑士礼,目光飞速打量了一下跟在后面的维奥雷尔。 伊斯雷还礼致意,走到围栏边,示意维奥雷尔也跟过来。 “这里是骑士团医疗处的办公室兼值班室。”卢佩恩轻声对维奥雷尔说,“从这里可以随时观察楼下的病房。” 的确如此——站在围栏边上,一楼的情况一览无余:病房明亮宽敞,窗前落着米白色的纱帘,房中放了二十张病床,但还余有相当的空间。病床大多空着,只有靠窗一排的五张上躺着伤患,都穿着淡青色的病服,其中三个在睡午觉,一个辗转反侧、不时发出压抑的呻吟,另一个在和一名巡房的医生低声交谈。 伊斯雷指了指角落里的一张病床。“您看得到吗,躺在那里的那位红发女性?”他轻声对维奥雷尔说。 维奥雷尔眯起眼睛勉力辨认了一阵,摇摇头:“太远了。” 陪同的那名军医拿下衣襟上别着的长柄眼镜递给他:“试试吧,也许合适。” 维奥雷尔皱皱眉,接过眼镜凑近眼前——有点晕,但的确清楚了许多:是的,一个年轻的女人,双目紧闭,脸色像地下室的莱维一样青灰覆满死气,苍白绷带从脖颈满满打下来不知延伸到何处,肩膀和锁骨附近有深红色浸染……他把长柄眼镜递还主人。 “带我到这儿看这个做什么?”他问。也许加上刚才眼镜带来的眩晕,这里弥漫的消毒水气味令他作呕,“这个女人快不行了。” “如您所说,她很可能再不会醒来了。”伊斯雷望着沉眠的女骑士,缓缓道: “即便真有万分之一的奇迹,肩骨破碎、伤及脊柱的她也将像现在这样,在病榻上度过余生。她曾经是一名有着优秀剑技的骑士,还不满二十岁,上个月刚刚订婚。为了从隼鬼喙下挽救莱维·库尔茨的生命,她付出了这一切作为牺牲,然后——”他看了看维奥雷尔,但是并没把后面的话说出来,重新将目光投向楼下的病床,“至于其他几个,他们也都在昨天下午的死战中身负重伤,虽不致丧命,但同样付出了血的代价……” 伊斯雷转过身来,深绿眼瞳攫住维奥雷尔的目光: “请您告诉我,这一切真的是必要的吗?” |  Valin Engner
Valin Eng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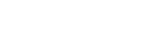




 发表于 2013-3-7 22:47:02
发表于 2013-3-7 22:47:02







 楼主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