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伊斯雷 于 2013-3-18 20:22 编辑
X
对于维奥雷尔·库尔茨来说,没有什么是必要的。 是的——对于一个自记忆伊始就不断逃亡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必要的,没有什么是不能舍弃的……母亲、莱维和他,三个人的逃亡并非朝夕迁徙风餐露宿,而是在日复一日的惨淡生活中努力远离那紧随身畔、挥之不去的可怖暗影。维奥雷尔至今仍清楚记得幼时在外祖父家那段令人窒息的日子:不要说永远对莱维和他视若无睹的表兄弟们,就连仆人和使女都不愿伺候他们,不但不为他们浆洗衣物、打扫房间,甚至连每天的食物也只是悄悄放在门口,仿佛踏入他们的领域便会被恶魔的气息所污染。如果不是偶尔发觉有人在拐角或柱后站得老远指点他们窃窃私语,他真会确信莱维和自己是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被女神所遗弃的幽灵。 母亲带着他们又一次逃离了,如上次逃离阿尔卡纳金枝投下的阴影一样——上次他们舍弃了秘仪尊贵的地位,这一次则是温饱的生活。新家破败拮据,而且日益拮据,加上一个时常酗酒的继父。他对母亲和她们这对双胞胎不好,但也不算太坏——比起彻底的漠视,一周一次的打骂还更令人心安,而且他至少还不反对母亲为别人缝补洗衣供他们上学,这在他们所住的底层市民区已经是令人艳羡的待遇。莱维和他已经满足。毕竟,他们不可能再逃到哪儿去。——城市之外的凶险荒野?饥饿的魔物们才不会蠢到真把他们当成什么恶魔之子。 只是偶尔,在十二三岁的青涩年纪上,他们会来到市中心大圣堂的广场前。夜幕降临,灯火初上,他们坐在灌木丛畔久久望着寂静空无一人的广场,脑海中有烈焰熊熊燃烧——那是将未曾谋面的父亲、以及他们的人生吞噬殆尽的冰冷火焰,照亮天际,灼干了他们脸上的泪痕。 很快他们连这少年式伤感的幻觉也舍弃了。否则,他们将无法面对那个根植于森染无所不在的名字,无法面对那些鲜衣怒马自他们身边傲然骋过的金枝少年们,无法抑制心中澎湃暗涌的、自己本应是他们其中一员的悲惨自艾。莱维成了一名精炼师,辗转于各个矿场,维奥雷尔则在市政厅谋到一份文员的工作。他们身被名为“库尔茨”的敝旧蝉蜕,低沉、灰败,悄无声息——这是恶魔之子苟活于世的正确方式。 继父早已去世,母亲则在去年中风一病不起。多年操劳不仅压垮她的身体,还碾碎了她的心智。她的神志愈发不清,总是搞不清回忆与现实,仿佛有什么东西紧紧攫住她的精神往时间的深渊拖去……终于有一天,她忽闪着迷离、松弛的眼睛,询问前来给她送晚饭的兄弟俩:他们最近不停在她房里进进出出,是不是新来的侍从? ……不——不可能!她苍老的脸上泛起少女式略带羞涩的惊怒:她的儿子们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他们可是赫赫森染执政官之子——他们将是所有金枝中最最睿智、优雅、勇健的那两个……! 维奥雷尔无言。仿佛揽镜自照一般,他转头看到哥哥扭曲崩溃的面庞。
大约就是从那时开始吧……莱维开始往那些油腻昏暗的小酒馆跑,一待就是整晚,将近天亮才摇摇晃晃摸进家门。但是他有阵子没有找到活儿了,钱包见底,他就开始时不时把人往家里带。酒馆结识的三教九流似乎更能鼓舞他的心灵。至于维奥雷尔——双胞胎兄弟之间本就无需言语,而每一次心领神会的安慰都是重复的伤害。维奥雷尔大致知道那些人用来鼓舞莱维的是什么:两瓶劣酒,一些“不无风险、但绝对保本带利”的小生意……维奥雷尔见过他们其中的几个,但并未加入过他们的筹划。作为公职人员,他必须谨慎,至于莱维……他无力劝言。他知道他已别无选择。 去吧——他坐在母亲的病榻前听着外间酒醉的喧闹,嘴唇无声翕动: 去吧,莱维,挣脱背负多年行将碎裂的蝉蜕,逃向那凶险未知的荒野…… 维奥雷尔·库尔茨抬起头来。 “那么,也请您告诉我——三十年前,我父亲杰克·阿尔卡纳的死是必要的吗?”他对伊斯雷说,目光和声音中有他未曾得见的火焰燃烧: “而您的父亲威鲁尔·阿尔卡纳恶毒的污蔑和告发,又是否别无选择?!” “库尔茨先生!请您慎言!”一旁的卢佩恩低声喝阻道。 伊斯雷抬起手,示意两人保持安静。 “我谅解您对先父的言辞。”他对维奥雷尔说,“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谈吧。”
XI
他们缓缓走在庭院中,脚下绿草如茵掩着一道碎石小径,前方是一株枝繁叶茂的菩提树在午后微风中婆娑如响。伊斯雷的声音和于其间,轻而分明。 “是的 。”他说。 维奥雷尔停下脚步。 伊斯雷转过身来,看着他因为愤怒而抽紧的面孔。 “这样的答案理应使您愤怒。但是我想知道,如果您置身于三十年前那场致命的汹涌暗潮之中,您又会给出怎样的答案?”他说。
准确地说,是三十一年前——莱维和维奥雷尔诞生于世的那一年。在年轻的杰克·阿尔卡纳夫妇为双胞胎的到来而欣喜时,暗云也悄然在整个阿泽兰王国的上空开始聚集。那暗云迅速酝酿成血雨风暴,在随后的两年之间将无数家庭、甚至家族引入破灭。 “伊迪斯名为‘狂王’,确然是个纯粹的疯子,所行生杀予夺并非出于理智,而是一己心情——虽然那情绪荒诞而不可理喻,但这样的人至少可以被激怒,也可以被取悦。”伊斯雷略一停顿:“然而卡拉米·泰勒绝非如此。” 既无家世、亦无背景的卡拉米·泰勒,能够一跃登上首相的高位,毫无疑问是逢迎了狂王的某种心意,但这绝不意味着他自身也是疯狂的。虽然人们不愿承认,但这个一向籍没无闻的男人的确有着卓越绝伦的心智——这一点在他所主导的大肃清中表现无遗:他以缜密而入微的思虑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如此周详切实滴水不漏以致对手无以自白;他深谙人之脆弱与恐惧,稍加拨弄便使他们热衷于相互怀疑构陷;他设下重重罗网引诱对手徒劳反抗,借以将他们逼入更深的绝境……暗探、密告、逮捕、刑讯、抄家、流放、死刑——这些交织弥漫成三八一年盛夏充斥于王都夏维朗的腐败气息,并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如剧毒般向其他四个城市蔓延,而这一切都出于卡拉米·泰勒精密、准确的操纵。 “卡拉米·泰勒的剧毒侵染秘仪,是三八二年的秋末。”伊斯雷低声道,声音中带着三分寒瑟,“也许出于谨慎,也许出于取乐的心理……总之,他把阿尔卡纳留到了最后。” 又或许,这才是卡拉米·泰勒真正的目标也未可知——阿尔卡纳是阿泽兰最为悠久、最为繁盛的家系,族人子弟遍布各地,与众多贵族联络有亲。一旦阿尔卡纳家倾覆,所将牵连者之众,绝非一般贵族可比。经过一年之后,异己者剪除将尽、幸存者噤若寒蝉,卡拉米终于着手炮制阿尔卡纳的罪状,而他所选择的引子,便是时任森染执政官的杰克·阿尔卡纳。 “我回答您令尊之死是必然的,是因为我们无从改变卡拉米的选择。至于他为何作此选择……身为族长的先父作为切入点太过生硬,而海德里恩伯父远在王都上议院,对塔菲鞭长莫及,他们两人虽然也同样身份尊贵,但并不是最理想的人选。——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测,至于卡拉米本人的真正想法,我们无从得知。”伊斯雷没有把最后的推测说出口:也许还因为,以年少得志、家庭美满的杰克·阿尔卡纳作为第一个牺牲品,能给卡拉米·泰勒带来更大的乐趣和满足。 其时身在夏维朗的海德里恩探知了卡拉米·泰勒即将针对阿尔卡纳的情报,但在严密的监视下,他不仅无法返回森染,甚至不敢寄出一封急件。——这个消息通过阿尔卡纳家仆的信息网辗转方才传回苍犀馆。 “也许您要质问,显赫数百年的阿尔卡纳家族为何如此无力?——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无力:在那疯狂的两年里,越是庞大的家族,就越无力,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他们所要面对的敌人,并非能以常理对抗。” 卡拉米·泰勒恐怖,因他是绝对的,这绝对的力量一方面来自他缜密的罗织,另一方面则来自‘狂王’伊迪斯的默许甚至支持,双重交织阻断一切抗辩、申诉和动之以情,使他立于不败之地,令人无法抵抗——一旦被这样的剧毒所侵染,任何挣扎都只会助长毒素扩散肆虐,加速死亡的降临 。 “如果是您,您是否有别的选择?”伊斯雷再次发问,但并未等待回答: “先父的选择正如您所知:他赶在卡拉米·泰勒发难之前奔赴夏维朗面见狂王,将计就计告发您的父亲为塔菲血宴的元凶。狂王对此欣然接受——他荒诞冷酷,但对一切激烈、夸张、违反人性的事物有着天然的喜好,并将此视为先父和阿尔卡纳家族对他尽忠的表征。正是以如此谬行换得狂王的庇护,才使整个秘仪家族免于卡拉米·泰勒致命的构陷。”伊斯雷的语速很快,声音压抑低沉。他看着紧咬嘴唇、神情恍惚的维奥雷尔: “我和您一样,并未亲身经历三八三年的灾难。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来自于先母临终的遗言。您可以质疑它的真实性,把它当成狡辩和开脱,这是您的自由,但我认为您有权知情这些。作为秘仪的族长,我必须向杰克堂叔、以及你们整个家庭为阿尔卡纳作出的牺牲致以最深重的感谢,以及歉意。——任何补偿都无法弥补你们的伤痛,但我们做的仍然远远不够——” 他退后两步,向呆立的维奥雷尔深深鞠躬,数秒之后才直起身来。 “——但是,作为威鲁尔·阿尔卡纳的儿子,我并没有什么需要向您道歉的。”他继续说,斩截而坚定: “先父付出了内心的安宁和个人的名誉,以及生命作为代价——他同样在烈火中化为灰烬,殊途同归。他所作的,和他所付出的,都已经足够。”
XII
维奥雷尔无法抑制自己肩膀的抖动。他双手满是冷汗,脖颈如针扎般微微刺痛牵动太阳穴连跳,脑中仿佛有重锤击打。刚才所听到的这些,他并非毫无心理准备——在尚未克制自艾的幼少时期,他曾经对父亲的死做过各种模糊的猜想,但在惨痛的现实面前,就连崇高牺牲也无法给他带来足够的安慰——彼时如此,现在亦然。他拒绝接受却又无从反驳,勉力开口,惊觉口中干涩,下唇已经粘在牙上: “我们的一生已经毁了,不必再惺惺作态。”他说,声音灰败空洞,“但莱维,他同样也无从选择。” 伊斯雷黯然。 “你不是就作出了另一种选择吗?”不远处,一个轻快的声音回答道。 维奥雷尔闻声僵硬转身。庭院一侧的廊下,蓝色短发、神情悠然的执政官正向他们走来,身后跟着刚才不知何时消失了踪影的卢佩恩。 “抱歉,那头多耽搁了一些时候。”利亚姆对伊斯雷说。他的头发已经抓松了,领口的丝巾也解开了,敞着礼服的绣金高领。他转向维奥雷尔露出微笑: “初次见面,库尔茨先生——或者我们都应该叫你‘堂兄’?我们要不要拥抱一下?” “我们早已经不是阿尔卡纳家族的人了。”维奥雷尔哑声道,用阴郁的眼睛盯着利亚姆——他在市政厅远远见过执政官几次,所以认识他:“您说那话,是什么意思?” “你们这对双胞胎一向命运与共,但此时此刻,一个躺在地下室,另一个则站在我们的面前——这难道不是因为你们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吗?”利亚姆看着哑然的维奥雷尔,挥了挥手:“我们来说点儿实际的吧。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精神上的忏悔,还是物质上的补偿……” “我们从来不需要阿尔卡纳的施舍!我们索要的是……”维奥雷尔怒吼着打断了他。他仿佛要说些什么,又仿佛被后面词语梗住了喉咙,嘴唇抖动着,目光凌乱不知所之。 利亚姆和伊斯雷对望一眼。 “我想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但是那样东西……”他用温和的声音缓缓说: “那样东西,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 并不存在——无论是无辜蒙冤自幸福巅峰跌落的杰克·阿尔卡纳,还是自甘骂名沉默前行的威鲁尔,抑或豁出性命换来背叛、正在滑向死亡深渊的夏拉·汶采尔身上——一旦跨过那道界线,就会明白那样东西不过是生者于此世执着的虚无幻影。 利刃高悬,无人幸免。 维奥雷尔灰色的双眼逐渐浑浊。他摇晃几下,以手撑树。四下寂然,惟有头顶菩提树叶瑟瑟如涛如嗟。 “送他回去吧。”伊斯雷对卢佩恩说。 卢佩恩走到维奥雷尔身旁,低声说了些什么。维奥雷尔摆了摆手,示意他带路,等卢佩恩走出几步,才直起身来,跟在他后面拖着脚步向长廊走去。 “维奥雷尔……库尔茨先生。”利亚姆从身后叫住了他。 维奥雷尔脚下一滞。 “我对你之前所作的那个选择表示尊敬。”利亚姆顿了顿,又说: “明天上午九点,我在治安官的办公室等你。” 维奥雷尔没有回答,继续向前走去。
伊斯雷和利亚姆站在树下,目送两人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他会去吗?”伊斯雷问。 “也许吧……但是别跟我打赌。”利亚姆拉了拉领口,把它弄得更松些:“不过黑市的线人那边也有了一些消息,这方面不用担心。倒是你……”他斜睨了堂弟一眼:“侯爵阁下这次是不是太苦口婆心了点儿?” “毕竟是上一辈的纠葛。”伊斯雷说。若是自己所作的决定,他是不会做出任何解释的。“——利亚姆。”他犹豫了一下,叫道。 “嗯?” “如果有朝一日,我也成为了有悖于这个世界的存在……你能像父亲一样,将我指认为恶魔,保护秘仪的周全吗?” 利亚姆看着淡然发问的伊斯雷。细碎阳光自枝叶间筛过落入那双深绿眼中,仿佛某种期待隐隐闪烁。他想起在老侯爵夫人葬礼上所见的那双眼睛——那一去无回的光,所指究竟是怎样的方向? 默默对视片刻,利亚姆走到伊斯雷身前,抬起手来在他额头上敲了个爆栗。 “我是不知道你要去干什么捣蛋的勾当……不过无论如何也不能教人发现了啊!干坏事儿的时候要怎么偷偷摸摸,哥哥我以前难道没教过你吗?”他抱臂看着手捂额头双眼圆睁的伊斯雷,笑了: “好像真的没教过呢——这样吧,晚上请我到‘雪松’喝一杯,我一定倾囊相授。”
Epilogue
维奥雷尔·库尔茨没有去见利亚姆。他缺勤了一天,次日一早到处里提交了辞呈,然后就离开了。自那以后,没有人再见过他。 在他辞职的第二天,一封记明莱维·库尔茨生前最后过往之人姓名、相貌的匿名信出现在警备队的投诉箱里。根据这封信中的情报和黑市线人所提供的消息,警备队抓捕了三名疑犯,但这个团伙的核心成员——包括那个被称为“老塞莫”的家伙,似乎已经逃离了森染。 “治安官已经向其他几个城市照发联合搜查请求和通缉令,圣盾之内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了。要么被捕接受制裁,要么就在荒野上四处漂泊,终有一日葬身魔物之腹——”利亚姆如是说,把堆在面前的高高一摞文书一件件甩推进挂着“待发”标签的文件篮,一边回过头看看窗外淡紫色的薄暮。 “——挺适合他们,不是吗?”他摩挲着下巴,露出洒然微笑。
夏拉·汶采尔死于三天之后。 她的骨灰被未婚夫撒入泪眼湖中,名字则镌上英灵塔灰褐色的花岗岩基座,在菩提树细密洁白如羽的花朵覆盖下静静沉眠——那是森染灵魂永恒的归宿。伊斯雷单膝跪于碑前,将夏拉的佩剑立于她的名字之侧。在他身后,骑士们肃然列队举剑行礼,铿锵之声在广场上久久回响。 伊斯雷轻轻抚过那些或熠熠闪亮生辉、或栉风沐雨多年、业已黯淡磨灭的名字——那些以血浇灌这片土地、于此生根结果的人们的名字。他逐一辨识着它们,心中升起一丝怅然——他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名字将不会被刻在这块荣耀的基石之上了;但他仍未知道,自己所将要付出的代价,是否足够。 他感到脸颊有几缕冰凉划过,抬起头来,微霾的浅灰色天空有细密银丝纷扬洒落。 森染的时雨不期而至。
--FIN-
== NPC Profile==
卢佩恩·嘉弗勒 昵称“卢平”(只有利亚姆会这么叫,作为真正上司的伊斯雷倒总是叫他的正名) 30岁,黑褐色头发,蓝色眼睛。圆圆脸,身材不高,微胖但并不臃肿,看上去和善而精明,比起军人,更偏向经纪商人的类型。性情温和,思虑周到,善解人意,总是面带微笑,似乎没有不能解决的难题。自伊斯雷出生起就担任他的侍从,也曾随主人前往王都两年,但中途便返回森染加入了骑士团,后来成为伊斯雷的副官。和利亚姆也很有感情。
莱维·库尔茨 终年31岁,褐发,灰眼。职业是祈理石精炼师——调配专用溶剂将矿石所含众多杂质溶解分离以获得高纯度的祈理石结晶,是介于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一种职业。长时间住在矿场,休假的时候才回到森染的家中。
维奥雷尔·库尔茨 31岁,褐发,灰眼,森染市政厅财政处的文员。 这对双胞胎是被认定为“塔菲血宴”元凶的杰克·阿尔卡纳之子。父亲在夏维朗被处以火刑时,他们刚满两岁。虽然秘仪家族为杰克的遗属做出了安排,但他们的母亲一心想要摆脱悲剧的阴影,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了娘家,并在他们八岁那年改嫁给没落贵族库尔茨。他们母子三人一生都在努力逃离秘仪眷属的身份。 作为“恶魔之子”,与生俱来的低劣感使兄弟二人形成了灰暗阴郁的性格,一直隐藏在名为“库尔茨”的壳下,但有一天这壳却被神志昏乱的母亲一言击碎了。精神失去庇护的莱维铤而走险,同样深受打击的维奥雷尔无力阻止,只能目送他离去。 莱维的死于非命使维奥雷尔积聚多年的怨恨爆发了。他决心向秘仪讨回父子两代人的公道,但这当然是徒劳的。就如利亚姆所说,无论是公道,还是他们母子一心想逃至的安宁的栖身之所,在这个世界都不存在。 维奥雷尔最后也没有谅解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但他似乎变得能够真正接受一些事情。对于他来说,这也许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威鲁尔·阿尔卡纳 伊斯雷之父,上代秘仪族长。血宴时任森染骑士团副团长。告发杰克被恶魔附身阴谋策划了塔菲血宴,获得狂王欢心,被攫升为骑士团长。经历了狂王的乱政、骑士团战争和皇位更迭,在政治风暴中努力维系秘仪家族的安泰。死于温斯特家的理魔法爆炸事故,终年43岁。
海德里恩·阿尔卡纳 利亚姆之父,威鲁尔之兄。血宴时任王都上议会议员。现仍在世。
杰克·阿尔卡纳 莱维与维奥雷尔之父,海德里恩与威鲁尔的堂弟,“卡拉米肃清”的牺牲品。血宴时任森染执政官,被威鲁尔告发为“血宴”元凶而处死,终年23岁。他其实是在王都夏维朗被处以火刑的,双胞胎在森染的广场上的追思只是错位的幻想。
夏拉·汶采尔 终年19岁,红发,蓝眼。富裕市民家庭的长女,性格刚强好胜,和某个小富商之子有婚约。为救莱维·库尔茨被隼鬼重伤,不治而亡。
米哈伊尔·萨特兰 25岁,黑发,褐眼。森染骑士团萨特兰小队队长。个性忠厚,但有时失于固执。对部下十分回护。
乔亚拉·博斯塔卡 17岁,亚麻色头发,褐眼。隶属森染骑士团的萨特兰小队的新入骑士。小贵族家的末子。性格活泼,对于分配的任务总是很欢快地去完成。虽尚欠稳重,但并不惹人厌烦。
约万·梅辛 28岁,红褐色头发,黑色眼睛。森染市政厅的助理治安官。行事一板一眼,容易流于套路,有些欠缺灵活性。
|  Valin Engner
Valin Engner
 Valin Engner
Valin Eng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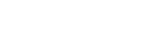















 发表于 2013-3-14 21:03:50
发表于 2013-3-14 21:03:50








 楼主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