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莱赫雅·巴泰拉 于 2017-10-13 00:50 编辑
Interlude IV
“这不对。”
拉夏德听见努尔·海普希这么说道。那个年轻的法祭眉头紧锁,紧盯着坐在椅子上的女人。闻言,女人转过头去看向他,笑容是温和的:“哪儿不对?”
“全部。你所叙述的一切都太过碰巧了。世界上是不可能是有这样的巧合的,它们只可能由人为引发。你一年前就知道下一次你来赌场的时候会撞上一个老千,又恰好捡到了从他口袋里滑出来得作弊道具;负责你坐的赌桌的女侍应生恰巧是你要找的人,而她又恰巧跟你在别的案子里认识?要编故事是足够精彩了,可是这一连串巧合在现实中发生的几率又多高,你想过没有?”
这些都是很正确的话,但不适合——拉夏德在心里评价道,事实上,这也是他自己的想法。但这些这不是一个法祭、至少不是一个负责审讯的法祭该说的话。就拉夏德看来,努尔很敏锐、观察力很强,但太过年轻急躁、沉不住气,而这样的人是钓不上大鱼的。
只见莱赫雅·巴泰拉冲他点了点头:“我愿意承认您说得没错。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年轻法祭的攻势就这么被化解了。他短促地咳了一声,好像是把原本准备好的腹稿咽进了肚子里,再另起一行:“你获取信息的方式也十分可疑。”
“请说?”
“根据你的叙述,你获取信息的方式主要是透过观察——可是你要怎么知道往哪儿看呢?事实上,不仅人类的主观价值会极大地影响侧写精确性,从一大群信息当中提炼出有用的部分、提供解释也相当困难。以一位失忆人士的身份而言,你的表现实在是太过优秀了,简直像是……你一直都知道该往哪儿看一样。”
这在统计学当中被称为离群值,往往不具有参考价值,你可能一直都知道相关信息,就像看着剧本去演戏——努尔用一本正经的表情跟眼神这么暗示道。这让拉夏德差点叹了一口气:法祭是谦卑的仆人,学识与技艺也不是能拿出来炫耀的勋章。越招摇的装饰,越容易被打落地上。
莱赫雅·巴泰拉饶有兴趣地抬起眼皮,用一种像是在估价似的眼神上下打量着努尔,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好像有火花在闪烁。过了一会儿,她舔了舔下唇,好像刚吃了什么特别美味的小点心一般开口:“父亲……不对,我猜是您的母亲?她在您小时候就去世了。您跟母亲的关系相当复杂,谈不上是融洽,不过她并不打你,我猜是忽略——”
有那么一瞬间,拉夏德觉得努尔的肩膀好像抖了一抖,但他马上便强硬地反驳道:“这些只要仔细调查过我的经历就能知道。”
莱赫雅噗嗤一声笑了:“您高估我了。我在这里已经被关了好些日子,又要如何得知被指派来审讯我的是谁呢?要是我有办法知道,岂不是意味着我连星之教会都——”
——渗透了?
她的声音还没落地,拉夏德已经一推桌子,猛地站起了身:“你跟我出来一下。”
“你不能让异端玩弄你——要想进行有效的审讯,你就冷静地得听他们说。他们说得多了,谎言自然便会露出破绽。”
拉夏德站在离审讯室门几米远的地方,盯着努尔的头顶训斥道。这年轻法祭的个子不高,体格也不太壮,比拉夏德足足瘦了一圈,脾气倒是跟年轻时的他一样倔。看着他时,拉夏德好像看到了那个还在跟着师长见习的自己。或许是这样,他才忍不住想要对这个毛头小子说教几句,哪怕这其实是他们第一次共事。哪怕拉夏德自认为自己现在的举止也称不上是法祭的典范。
“可是!您都已经听她讲了三张羊皮纸长的故事了!”努尔将手背在身后,低着头抗辩道,声音越来越激动,“您真的相信她那一套鬼话吗?!什么会唱出让人感觉不舒服的无声歌曲的鸟、什么戏法的原理……还有,她居然说什么’一定要按顺序说才能让你理解’!放屁!这不是在扯谈是什么?傻子都能看出来!”
拉夏德面不改色,只是折起手中的羊皮纸装进信封里:“注意你的态度,年轻人。”
“……哦……对不起。”
他老老实实地道了歉,这点倒是比从前的拉夏德优秀,因此拉夏德也不打算太过为难他:“低头看看吧,你的挂坠盒露出来了。这不符合着装规范。”
努尔低头一看,连忙伸出手,将那个用金色链子拴着、带着女性画像的小物件塞回红色的法祭罩袍底下。他放下手,恍然大悟似地喃喃道:“所以,她就是这样得知我——”
“没错。”
那是张泛黄褪色的画像,意味着这个挂坠盒曾经长时间遭到放置、暴晒,链子也有些脏,充分表现出物主跟画中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努尔现在贴身戴着这个挂坠盒,说明他仍然对她有些执着——莱赫雅·巴泰拉或许是这么推断的。拉夏德读不了她的心,只能试着模仿她的思维方式,尽管他也说不好她究竟是不是这样得出结论的。
“也就是说,”努尔颓丧地垂下了双肩,“这些其实都是很容易就能观察出来的,我在一个异端面前闹了笑话。”
“不,这并不容易,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这不是安慰,只是事实,“还有,有件事你说对了。巴泰拉的确在说谎——至少她的故事里有一部分是谎言。”
“什么?”
拉夏德几乎叹了一口气:“我知道‘费丝·瓦力’是谁。”
他看着努尔慢慢抬起头来,那双湛蓝色的眼睛一时间好像找不到焦点,瞳孔微微扩散。努尔抿了抿唇,喉咙间挤出了一个短促的音节:“谁?”
“一个幽灵。”
“幽灵?”
“比喻,”拉夏德将视线向右上方偏了偏,就好像那儿写着提示,“你要知道的是,‘费丝·瓦力’已经死了,死了很多年了,有二十年了。她是个异端,带着伪神的旗号害了好几个家庭,后来被绑到火刑架上烧了个干净。然后苏利斯山庄……苏利斯山庄是她的藏身处,法祭就是在那儿逮捕她的。”
纷飞的火焰。沉默的女人。莱赫雅·巴泰拉至少说错了一件事,那就是苏利斯山庄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费丝·瓦力就是从她藏身的橱柜暗格里被拖出来的。
“可是这个叫费丝·瓦力的……是真的死了?”
“是真的死了。因为给她脚下的柴堆点火的人,”拉夏德迟疑了片刻,“就是我。”
努尔不说话了,只有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好像在努力消化拉夏德刚刚说的内容。不过,有一件事拉夏德没有告诉他——费丝·瓦力不仅仅是个异端,至少对拉夏德来说不仅如此。
她还是害了拉夏德全家的凶手。
说起来,拉夏德·邦威特本不该成为法祭。按照父母的计划,他应该去都青府上学,结交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以便以后在宴会上能提到他们。他毕业后最好能调回来尼恩格兰骑士团,这样即使是算不上豪门的邦威特家,也能给他打点好关系,让他仕途无忧。然后发生了什么呢?他接到了从家乡来的急信:一位“好心人”向狂王的走狗检举了他的父母。一周内,他失去了一切,一年后,拉夏德踏上了圣域的天梯。四年后,他知道了仇人的名字——那是个在他小时候经常出入他家、与他的父母密谈的女人,大约是为了自保而做了污点证人。于是七年后,拉夏德把她送上了火刑架。
“所以,”他总结道,“要是她还能作乱,那不是幽灵是什么?”
“可是费丝·瓦力可不是什么常见的名字,恰巧重名的几率很低。所以要么是有人冒用她的姓名——”
“——要么是巴泰拉在胡编乱造,或者诚心想刺激我们。”
努尔伸出一只手,擦了擦鼻尖和额角冒出来的汗:“可是这也说不通呀!也太巧了吧?谁会冒名顶替一个异端呢?而且,您是主理案件的法祭,而这个案子里恰好就出现了……”
他没有再往下说了,但拉夏德知道他想说什么。无论是有人冒名顶替费丝·瓦力,还是巴泰拉自己在说谎,要让“费丝·瓦力”成为喉中之鲠,得先满足一个条件——得有人知道拉夏德跟费丝·瓦力的关系、以及他将成为主审法祭的事实。但是究竟由谁来主审,却是在逮捕莱赫雅·巴泰拉的当天才决定的。身在尼恩格兰的法祭人数众多,偏偏是他?这怎么看都只能用巧合来解释——可偏偏是费丝·瓦力?狂王之乱之后处决了这么多异端,偏偏是她?
“主审法祭的任命虽然紧急,却不是随机的。可能是巴泰拉背后的势力在任命人选时动了些手脚,也有可能是收集了所有身在尼恩格兰的法祭的资料。不管怎么说,总有会有可行的办法的,只是我们现在还暂时判断不出来。”
“但那不就意味着……”
“我知道,”要是那股势力真能做到这种地步,就意味着他们有能力渗透星之教会,拉夏德发自内心地祈祷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其中几种假设——比较糟糕的几种。”
“还有更糟糕的吗?”
“当然有。”
“比方说?”
“比方说,这些事情当中有恶魔参与。这样的话,这案子可就要划归封魔省管辖了。”
努尔的眼珠子又滴溜溜地转了一圈:“您是在说,二十年前被烧死的‘费丝·瓦力’其实是个恶魔,现在她又回来了?所以巴泰拉遇到的那个人才会自称是费丝·瓦力?”
拉夏德没有作声,他又继续嚷嚷道:“可这样也很奇怪呀!她是怎么知道巴泰拉会被您逮捕……哦,您的意思是,他们是一伙的?她是巴泰拉的上级——”
“我可什么都还没说。不过,以防万一,”他慎重地拣选着自己的用词,“我们得向上面报告一下这件事,就说我们怀疑这件事情牵扯到了恶魔,需要星士来处理……信我已经写好了,我会派英格维德去报信的。”英格维德是那个正在房间里看守巴泰拉的见习法祭的名字。
努尔口中喃喃了几声,忽然“啊”地叫了一声:“英格维德,英格维德……阿蕾瑟·英格维德?”
“是的。怎么了?”
“巴泰拉说自己赌博用的假名可不恰巧就是‘阿蕾瑟’吗?这也不是个常见的名字,我听的时候就觉得有些奇怪了!”说这话的时候,他往门那边瞟了一眼,看上去比刚才还要焦虑,“前辈,您说,该不会——”
拉夏德没有马上回答。但他能感觉到那种令人不快的寒意又从脚底开始向上蔓延。巴泰拉形容得对——他痛苦地承认道,这件事情真是越发越诡异了,他很确定自己正在处理某种规模庞大的事件,却摸不清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什么,就好像有一张无形之网从天而降,将他——将他们笼罩其中,慢慢收紧,令人窒息。
他不知这是不是偏见,可他越发觉得莱赫雅·巴泰拉的笑容跟费丝·瓦力有几分相似。那个女人从不认罪,从未忏悔,在被绑在火刑柱上时也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很抱歉,可我已经发过毒誓,要永远保守秘密……”
她说这句话时仍然是平静而放松的。那不是属于将死之人的表情——就仿佛她并非站在柴堆上的死囚,而是接受觐见的女王……事到如今,拉夏德总算是摸清了自己打从一开始就不太待见莱赫雅·巴泰拉的理由。费丝·瓦力已经死了很久了,久到拉夏德早已能平静地将她丢进记忆的角落,让那张脸蒙上灰尘。可是如今,那些尘埃又出乎意料地被那张巨网搅动起来,在他的眼前四下飞舞,令人心烦意乱。
——然而,真的有人能设置出如此复杂而周全的……阴谋吗?
“不要做无谓的猜想,”拉夏德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对努尔、还是对自己说这句话,“不要妄下判断。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其他的……就交由星士、交由女神来决断。”
女神总是在注视一切,无论那张阴谋之网织得有多么细致绵密,她都会有拆解她的方法。要清理蛛网,首先就得对付盘踞网上的蜘蛛……可是,蜘蛛究竟指谁?莱赫雅·巴泰拉,费丝·瓦力,还是别的什么人?
“那么,前辈,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要一直等到星士来接手这件事吗?”努尔的声音打断了拉夏德的思考。
“不,那样太慢了,我们继续审问她。听着,我要你忘记我刚才跟你说过的话——或者说,在巴泰拉的面前,装作忘记我对你说过的话。我们应当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从来不知道费丝·瓦力是谁。假如处理得当的话——假如巴泰拉的确知道费丝·瓦力是被我处决过的异端、因而有意提到那个名字的话,她这个时候理应感到疑惑,从而有机会露出马脚。懂了吗?”圣域离尼恩格兰并不远,假如一切顺利,这场审讯恐怕会比他所想的要更早结束。
努尔点了点头,不过拉夏德觉得他看上去有些不太甘心——这很正常,年轻人总会想着建功立业,拉夏德当年也一样。他想了想,又补充道:
“不过这一次,我们改变一下策略。每当莱赫雅·巴泰拉停下话头,你便要去挑她话里的毛病。而只要她一反驳你,我便应该出声平息事态,让她继续往下说。”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施加压力。处在压力之下的人类更容易犯错——我们要她犯错。我们要从她的话中找出线索和破绽,拼凑出事情的全貌——赶在下一起案件发生之前。”
审讯室里的一切都跟他们离开时一模一样:莱赫雅巴泰拉被铁链锁着,固定在椅子上,英格维德则站在离她一步之遥的地方,手按在剑柄上,好像随时都能将那罪人一刀两断。拉夏德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将那封信塞到她手中,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门外,才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拿起羽毛笔和羊皮纸。努尔则像是他们说好的那样,代替英格维德站在莱赫雅的背后。
“您回来了?”莱赫雅·巴泰拉看着他落座,又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啊,抱歉,我是真的累了……那么,事不宜迟,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吧。”
“下一个环节?”
“招供呀。我相信您会喜欢接下来这个故事的。毕竟——”
她眨了眨眼,脸上的笑容忽然消失了。红发女人挂着一副严肃的表情,庄严地、甚至能称得上是凶狠地宣告道:
“——就像你们逮捕我那时发现的那样,我可是货真价实的杀人凶手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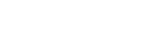
























 发表于 2017-8-27 21:09:21
发表于 2017-8-27 21:09:21








 楼主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