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法泽雷尔 于 2013-3-7 12:04 编辑
法泽雷尔 法泽雷尔·费特摸了摸自己一头枯黄短发。手指的触觉让他陌生,原本长而卷曲的银发不见了,如今他的脑袋像是一丛杂乱生长的杂草堆,还有些地方薄厚不均……
“小心。”红隼抓住他的手,“多摸几下的话说不定就掉色了。”
“我们还有多久?”
在红隼家住过一晚上后,第二天法泽雷在太阳尚未升起时就起床了。红隼来到露台上的时候,他正收起谶言。蓝色的晨雾将他完全包裹住了。他和红隼的身高相当,但是要强壮一些,因此他穿着的是红隼那件打补丁切宽大的旧上衣短袍。腰间的皮带也已放在红隼家的床下,少年以暗色麻布捆住箴言围在腰上。他的靴子也换成了黑鼠窟里最常见的破烂的布鞋。
“你起得太早了。洛托可不会这么急着召见我们。”红隼朝他丢过一块干酪。
“我的剑术老师说,一个伟大的骑士应该每天磨砺自己和他的剑。”法泽雷还有些气喘吁吁地擦去额间的汗水,一边对着那块干酪咬了一大口。“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和你们相似了?”红隼打量了他一会儿,然后他伸手从墙上抹了一把。“这个会让你更像。”他将手上的青苔和泥水擦在法泽雷的脸上。“你今天早上没洗脸吧?”
“没有呢。”法泽雷尔只感到脸上凉凉的,如果被我父亲和导师看见我现在的样子,他们一定会气得暴跳如雷吧。想到此处的法泽雷尔笑了出来。去他的。我现在可不是法泽雷尔·费特了。
昨晚红隼和他一起想了个故事。那是关于一个叫做雷尔的孤儿的故事。这是他新的名字。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矿区的工人。最后死于一场魔物的袭击。他本来一直跟随着父母住在矿区,所以不住在黑鼠窟。直到骑士们将他和幸存者们一起带回尼恩格兰。他才决心在这里找一个可以活下去的工作。
红隼对于这个故事相当满意。法泽雷尔则花费了整个晚上,在黑暗中紧张地思考还有什么细节遗漏。“长脸”洛托是个狡猾而残忍的家伙。红隼告诉过他。没有什么秘密能在他面前隐藏。对于这个突然冒出来想要加入的小子一定会多加怀疑。我必须忘记自己是神使之子。法泽雷尔心想。忘记法泽雷尔·费特。我是矿区的孩子。是被魔物夺去了父母的孩子。我是个孤儿。
那个词如同一记重击打在他心上。真是讽刺。我本来就是个孤儿。我甚至连我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如今我却要扮演本来的我自己。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加讽刺。
所以当他们用完了早餐。一起来到洛托所在的那间旧仓库面前时,法泽雷尔已经消失,只有枯黄色头发,脏兮兮的雷尔和红隼同行。
房间里有四个男人。洛托很好认出。因为他一见到红隼带着雷尔进来就露出暴躁的表情问:“这是谁啊,才一天你就交到了新朋友?”雷尔发现他盯着自己腰上的佩剑直打量。这实在不像是一个孤儿所会拥有的东西。他暗自冒出冷汗。但是他需要箴言。必要的时候。他想。不知为何,离开谶言似乎让他觉得自己虚弱无比,就要淹没在这个远离圣域的地方似地。因此看到洛托如同尖刀的眼神在他周身打量时,法泽雷尔努力忍住控制住自己的腿不颤抖,他只是佯作无辜地笨拙地鞠了一躬。
“这是雷尔。我昨天去探查的路上遇到的家伙。”红隼及时替他开脱,“昨天我拿了……那几个守备一点钱。要不是他我就死啦。”洛托露出一个没有温度的微笑,“你失手可真是少见啊红隼。”“昨天人很多。”红隼回答道,然后他挽起袖子,把那瘀伤展示给洛托查看。“看见没,他们差点把我打死。”
那是昨晚法泽雷尔用剑鞘捅的。 “你完全不必这样……”法泽雷尔拿着箴言,“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控制力道。”
“快动手。趁我妹妹不在。她要是一会儿回来一定会尖叫的。”红隼脱下上衣。“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觉得肚子也要抽两下才好。洛托一定会怀疑的。相信我,你要是没能骗过他,我们两个都没好果子吃。”
于是法泽雷尔用箴言狠狠击打红隼的手肘和腹部。直到那些淤青可以被看见。
“还有我的。”然后他把剑递给红隼。“对,就像握住一根树枝那样,拼命打就可以了。”然后他也褪去上衣,直到他们两个都伤痕累累。
洛托看似漫不经心地检视着红隼的伤口。他还抱有怀疑。法泽雷尔绝望地发现屋子里另外三个男人也在注意他们。一个胡子拉碴的黑发男人正在用磨刀石磨他的那把长剑,一边朝这里投来阴冷的目光。另一个男人则抱着竖琴,好奇地朝这里观望。而角落里的那个最令他不安。那个如同阴影一样的男人靠在墙上,嘴里噘着烟叶,他没有看向这里。但是他其实在侧耳倾听。法泽雷尔想。那是个朝灵。最奇怪的是,他们三个的穿着看起来比洛托要高级很多。衣着材质都不像是黑鼠窟的人能买得起的。
“我可不喜欢随意乱看的小老鼠。”法泽雷尔发现洛托把目光转向了他。那男人有一张油腻腻的长脸,脸上还有一道可怕的刀伤。神情里透露出一股常年混迹在土匪和扒手中才有的残忍的狡猾。 “你叫什么。” “雷尔。”他平静地回答。
“唔。我之前没有见过你。”洛托摸了摸自己胡渣丛生的下巴。“这里每一个孩子我都见过。我可不记得你啊。”
“我一直和我的父母居住在尼恩格兰城外的矿场上。他们都叫我‘煤渣’。”雷尔是不会恐惧的。他提醒自己。“我本来是要和我的父母一起回尼恩格兰的。但是我们的队伍半路上被魔物袭击了。我的父母……和我的弟弟们都死了。”
“所以你就一个人回来了?”
“骑士大人们救了我和其他人。我听说我的父母以前也住在这里。所以我想回来碰碰运气。”法泽雷尔努力使自己的眼神看起来空洞而麻木。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你可适应得挺快。这年头真是没个准儿呢。是吗?”洛托露出一个锋利地微笑,指了指法泽雷尔腰间的那把剑,“也许你还可以告诉我,一个矿工的儿子怎么会有一把这么漂亮的家伙呢。”
“我偷的。”他努力克制自己想要握紧的拳头。雷尔是个孤儿,是个坏小子。他不会在乎的。“我的父母……”他耸了耸肩膀,“我的弟弟有些太多了,先生,如果你想打听这些的话。老实说我都觉得有些过多了,我都叫不上他们的名字。我的父亲是个酒鬼,不上工的时候就喝得连他老婆都不认得。我的母亲吝啬又愚昧。”他露出一个微笑,“您一定不会奇怪我为什么没有妹妹吧。在有些姑娘稀少的地方,女儿就意味着可以换一袋土豆。”
他看见红隼眼睛里悄悄的讶异。这是他们之前没有编过的细节。是啊。法泽雷尔心想。这些都是法泽雷尔·费特所没有经历过的人生。但是他听闻过,他见过。有一次,当他还是神使的儿子。坐在温暖的马车里招摇过市的时候。他见过那些路边的乞儿和少年扒手。当时一阵难以言喻的愧疚就将他的心紧紧攒住。
我本来也应该在那里。神使之子想道,那里有我的一席之地。如果不是我恰好被父亲收养,我也会变成那种样子。如今一道马车的门却将我和我本来的命运隔开。虽然这应该感谢女神,但不知为何,看着那些眼睛,我无法面对它们。于是他记得自己是怎样焦急地把马车窗帘遮上。不去看他们。
他做过无数个噩梦都和这些多么相似啊。他想。我只不过是说出我的恐惧,说出我也许逃避了的命运。
“看起来倒是令人惋惜啊,小子。”洛托伸出他那双骨节粗大的手,摸了摸法泽雷尔脸上的泥巴,“不过你的身手如何啊。我这里可不养活窝囊废。”
“我父亲曾想让我加入矿上的雇佣兵团。后来他们说不收我这样的小个子。”法泽雷尔说,“但是我像矿上的铁匠学过剑术。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偷一把剑的原因。”他做出一个狡黠的微笑,“我十三岁了,先生,知道什么地方需要剑。”
“看来红隼替我找了个聪明小子。”洛托拍了拍法泽雷尔的肩膀。“不过小子,话说在前头。说大话的混球我可不是没见过。眼下正好有一件事需要你去为我跑腿。如果你能办好,那么我就可以考虑一下。”
是试炼。法泽雷尔冰冷地想。他从那双眼睛里读出了不信任。
“最近城里有些骚动。”他说,“在附近有一个值班警备队的休憩所,很好认,那种圆圆的石头房子。我要你去那里为我拿回一份报告。去找一份最新的命令。没猜错的话应该就在那张桌上。”他摸摸下巴。“红隼知道那间温馨的小屋何时没有人。他也知道如何开锁。他会带你去那里。其余的你得自己搞定。”洛托说着,挑战地看向法泽雷尔,“小子,别怪我没提醒你,如果你被那些警备队发现了,你就只能自求多福。我想最好的选择是干掉那些蠢蛋。”洛托似乎想起了什么:“当然罗,你也可以束手就擒,然后说是黑鼠窟的洛托大人让你来的,不是吗。但是那些穿袍子的家伙才抓不住黑鼠窟里的这只大老鼠呢。”他露出一个凶狠的笑容,“可这只老鼠却知道不少此处的地道。如果有一只小老鼠想要告密,说不定他的小脖子明天就被扭断了。”
“我知道,先生。”法泽雷尔点点头。
之后他和红隼一起走过几条街,才终于到了那间屋子前。
“这个时候。”红隼看看天空,判断着时间。然后他们就装作路边的两个贫民窟孩子似地闲逛过去。果然,有两个穿着警备服的男人从屋子里走出来。其中一个身上还有着一股酒气。
“嘿!臭小鬼,别在这里碍事儿。”那两个人看见红隼和法泽雷尔半是取乐半是粗暴地轰走他们。用脚踢男孩们的屁股。法泽雷尔和红隼匆匆躲开。跑远几步之后,法泽雷尔听到身后诸如“这些该死的小扒手”“苍蝇”的抱怨。当他回过头的时候,那两个男人已然走远。“来吧。”红隼催促道。“现在那屋子里没人。”两个男孩绕过正门,直奔藏在暗巷之中。
“这里有一道后门。”红隼在那扇有着一把锈迹斑斑门锁的木门前停了下来,从衣服里掏出两把生铁开锁器。开始在那个小孔里咔哒咔哒地探测着。法泽雷尔好奇地探过头来观看。“这……我父亲说这是小偷的行为。”虽然他喃喃说着,但是语气里好奇的口吻却战胜了责备。
“这是‘懒鬼’教我的。他爸是干这行的老手。他曾经声称,他爸要是乐意,准能连那些贵族夫人的贞操带都能打开。”红隼咔哒咔哒地摆弄着。
巷道里这会儿没人。只有开锁器在锁孔里的碰撞声回荡。如果父亲知道我现在穿着破衣服,正在和朋友一起撬警备队的锁,不知道他会怎么骂我呢。法泽雷尔一边想着,一边入迷地看着在那两根小棍的拨弄下,锁头咔哒一声松了开来。 去他的。法泽雷尔在乎这些。但是来自矿场的雷尔不会在乎。
“好了。”红隼替他打开门。“我得走了。洛托说我只能帮助你到这里。之后你要尽快在里面找到他说的那份文书。那两个醉鬼这会儿巡逻去了。一会儿就会回来。你记得回去的路吧?”
“我记得。”法泽雷尔点点头,跳进了那扇门里。“谢谢你。”
“嘿,这比起你两年前做的,算不上什么。”红发男孩替他关上门。法泽雷尔知道他一定在关门后如同貂一样窜走了。这些黑鼠窟的孩子都犹如夜猫一般的行动力。
屋子里很暗。窗帘半掩着。还有一股酒味儿。一张上了年头的橡木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杂物。磨刀石,几个用旧的剑鞘,几枚铜币,一袋空酒袋,好几卷羊皮纸和几只羽毛凌乱的羽毛笔。在那边上则是堆满了各种积灰卷宗的橡木书架。只要一碰就会扬起一阵灰尘。法泽雷尔翻看了几卷就已经被呛得打了喷嚏。那都是些陈年旧令了。男孩摇摇头,随手把这些扔在那张橡木桌上。
他打开抽屉,里面有一叠羊皮纸。最上面一张有一个无比熟悉的封蜡纹——那是圣域的。少年拿起那张羊皮纸。上面的文字里有他和他弟弟的名字。还有外貌。这真奇怪。在这里拿着一张寻找自己的启事。他想。然后他看了看日期。叹息一声。将那卷羊皮纸卷成一捆,放入自己的缠腰布里。
然后他听见了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
少年的心脏狂跳起来。会被捉住。他四下张望。终于发现在那个布满灰尘的书架似乎还能一用。于是在那扇门打开的一瞬间。他手脚并用,从桌上爬上了书架顶端。书架发出了一阵轻微的嘎吱声。他的周围都是些蜘蛛网和卷宗以及大量的灰尘。书架够高,因此他几乎快要贴到房顶。没有点灯的这间房间内,他所栖身的地方正好被黑暗所笼罩。少年努力忍住鼻子的搔痒。一手紧紧握住箴言的剑柄。紧张地盯着那个穿袍子的身影。
“你有没刚才听到什么声音?”一个守备队员走了进来,边走边问他站在外面的同僚。就是那个一身酒味儿的家伙。
“大概是老鼠吧。”外边那个不耐烦地说,“这地方迟早要被老鼠咬穿。我有点口渴。要不我先去‘金号角’那里买一杯酒等你?”
“嘿。这倒是个好主意。”屋子里那个说,“再让那个大胸部的侍女给我来盘烤鲑鱼。”
门外那个懒洋洋地答应一声,法泽雷尔听到他走远的声音,盔甲踏在地上发出的碰撞声。
眼下的这一个倒是不慌不忙地在一堆杂物里翻找着什么。“啊哈。有三枚。”法泽雷尔发现他从一本泛黄的旧账本下发现了三个铜币,这家伙自言自语地把那三枚铜币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继续搜寻这里有没有遗落的铜币。
扬起的灰尘让躲在书柜上的少年苦不堪言。在最终他没能忍住,打了个喷嚏。
“谁!”那家伙拔出剑的一刹那,法泽雷尔的身体比他的大脑更早做出了反应。他从上方扑向他,人们经常会担心身后,却极少往头顶上看。少年一下子将那男人扑倒在了地上。他身上的灰尘掉到了对方的眼睛里,那家伙流泪不止地破口大骂边挣扎边踢来踢去。法泽雷尔一只手握住剑柄,另一只手按住对方的脸。同时用脚去踩那警备队员的握剑的手。
干掉他啊。法泽雷尔心里有个声音在那一瞬间说。趁现在,干掉他。完成任务。然后我们就能加入血乌鸦,救出洛克斯。只要现在,干掉他。
他从未想过死亡来得如此迅速。他从未杀过人。“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已开荤。”他想起克鲁茨对自己这样说,“你还不适合……你,还没到时候。”他教给他所有的技巧,他知道有一天这些技巧绝不再是为了打架取胜,总有一天他的剑上会染上鲜血。长久的训练,无数个清晨地拔剑,男孩心里隐约觉得他一直在为了某一天做准备。
那么现在是时候了吗。他不是法泽雷尔·费特。他是雷尔。一个一心想要救出弟弟的孤儿而已。手里恰好拿着剑。只要他杀死这个守卫。就能证明他的胆量和决心。他突然明白洛托那时候语句里的狡黠,取得这份文书是一方面,而证明自己是另一个方面。他的意思是,要通过杀戮,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决心。
没有什么比一条命更妥当的加入保证了。如果他真的是矿区的雷尔,那么他自然不必受荣誉和良知的约束,就像黑鼠窟的其他人一样,只要杀了眼前这个警卫就行了。他内心身为哥哥的那部分,要他立刻动手。机会转瞬即逝。
少年拔出箴言剑。几乎就要动手。
【我们的言行必为我们判罪。】
在一瞬间,他看到那剑身上的箴言。少年高举起手中剑。
然后他用剑柄打了那男人。一下在头上,两下在脑门上。那男人挣扎着转身的时候,他最后一下敲在那男人的脖子上。直到对方昏了过去。
当他从后门走出那件屋子时,几乎是像个落魄的乞丐一般奔跑着的。他才发现自己也浑身伤痛。
你这个笨蛋。他心里有个声音对自己说。你平日里的聪明和机智哪里去了。洛托说只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杀死对方。要么被对方逮住。这下你只是打晕了他。那个男人会很不满意。他会怀疑你。然后你就永远也别想找到洛克斯了。
更糟糕的是。他想起自己答应丽芙的事情。不要把红隼卷入危险的事情。
对不起。他边跑边觉得自己的心渐渐被愧疚和恐惧攥紧。为了那一瞬间的善良。也许我会害死更多的人。然而我无法下手杀死无辜的人。纵使那是个酗酒又暴躁的陌生人。他的命也许和我弟弟的命都放在一座天秤上。但是……他想起父亲对他说的,在女神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们都受到女神的爱和庇护。所以他的右手。他憎恨而懊悔地跑着,所以我的右手不听我的话。他奔跑着。穿过一道道黑影。
对不起。我做不到。洛克斯。他停在洛托那间仓库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脸上不知何时已经泪水和泥土已经糊成一团。
如果我不回去……红隼会有麻烦。他想。擦了擦自己脸上的泪水。我可以告诉那男人,是因为我的怯懦,我还是个孩子,我从未杀过人。我会求他放过红隼。他想。圣域的法泽雷尔从来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
当他正要推门进去的时候,刚巧看见一位红发少女从门内出来,身上却带着血腥味。男孩呆愣了一下,差点和那个红发少女撞到。那少女只是看了一眼法泽雷尔,就扬长而去。然后他听见屋子里洛托的声音。
“看来你的任务完成得不怎么样啊。”那男人促狭地说。衣服上还有些可疑的血迹。是新鲜的血。法泽雷尔心里抽紧。
“是的。”他掏出那卷羊皮纸,发现上午还在仓库里见到的三个男人都不见了。他努力试图寻找打斗的痕迹。但是除了洛托身上几滴可疑的血迹之外一无所获。该回到我自己的事情上来。“我……打晕了他。但是我发誓那人没看到我。我当时浑身都是灰尘,他的眼睛被灰尘迷住了,我很确定。”男孩急忙地解释着。
“谁知道呢。”洛托懒洋洋地拿过那卷羊皮纸,打开之后扫视了一眼就把它丢开了。“再说一次你来自哪里?”
“我来自矿场。”他回答。
“好吧……矿场。”洛托站起来,“小子。你不会是见不得血吧。”
“我……我从没杀过人。”他回答。“我只是想混口饭吃而已。”
“想必红隼那小子告诉过你,我这里需要人手吧。”洛托说,一边注视着法泽雷尔的眼睛。“你哭过,小子?”
“我太害怕了。”他回答说,“我当时太害怕。灰尘也掉到了我的眼睛里。”他的身上的确还满是蛛网和灰尘。
“在我们这种地方。”那男人缓缓地说,“‘害怕’是一种奢侈的东西。小子。”男孩静静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审判。
“所幸,那三个讨厌鬼没什么利用价值了。而我实在是需要新的人手。”法泽雷尔意识到他说的那三个人应该就是上午还在此地的三个男人。他将他们都杀死了?他看着这个脸上有着刀疤的男人。就凭他一个人?
“小子。你合格了。”洛托突然说。
“什么?”法泽雷尔还没有反应过来。愣愣地看着洛托。
然而那男人的眼神像是隐藏着什么。
他说:“如果你真是个胆小鬼。你这会儿已经逃跑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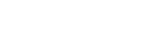




 发表于 2013-1-23 21:03:40
发表于 2013-1-23 21:03:40
















 楼主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