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法泽雷尔 于 2013-3-7 12:11 编辑
法泽雷尔 他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醒来的,或者这又是一个梦境? 可笑的是那个梦让他觉得比现实更加真实,在梦里,他是来自矿上的孤儿雷尔,他的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强壮男人,他叫他阿雷。他从五岁开始就学会如何当个出色的扒手了,他偷能够偷到的一切。别人的梳子,某个人的茶杯,甚至是鹤嘴锄。他也不知道为何自己要偷窃,就像他从未思考过自己活着的意义一样。有什么区别呢,对他们这样的男孩来说,故事里的城堡或者是骑士都是一个个符号,在这里,做梦的人他们会让你永久睡去。
离他比较接近的事情是,每天早上父亲如雷一般的鼾声和屋子里经久不散的酒精味。衰弱的母亲每天都要擦拭的木头女神像。还有没完没了的啼哭声——那是他的妹妹。如果不是将来能卖个好价钱,他的父亲大概会立刻把这些小东西丢出去。对阿雷来说,一个妹妹也许就等于一顿有肉食的晚餐,或者一件新玩具。这就是他所有关于血缘最初的记忆。 偶尔有几个女神的司祭来这地方,可是大家都把他们当做取笑的对象。只有他的母亲会尊敬地称呼他们为“大人”,并向阿雷形容圣域是个如何恢宏的地方。 “那里人人都和善友爱,女神的圣域圣洁又安宁。”他的母亲这样告诉自己的儿子。 “……那里有吃的么?”他问母亲。 “噢,好多好多吃的。神使大人每年不都会在冬天差人送东西来吗。女神是仁慈的。” “那太好了。”他说,对于阿雷来说,圣域是个可以吃饱的地方。 后来他的双亲都死在了魔物的爪子之下。男孩甚至连他们最后的表情都不记得。到处是受惊的马匹和人群,他看到有个什么东西把矿上的一个小伙儿拦腰撕开,就好像他们早餐撕开黑面包一样。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男孩跳进一口枯井里,把自己藏在干涸的井底。直到他听到外头传来兵器和冲锋声。后来有个闪闪发亮的手臂朝他伸来。 “嘿!这里还有个孩子!你没事吧!”那个带着好看头盔,擦得比他们家盘子还亮的盔甲的男人这样朝他喊。 他没有回答。他们以为他在害怕。于是把他像个小动物一般护送回了尼恩格兰。 他惊讶地发现这座女神脚下的城市,并没有充满食物和喜乐。后来人家告诉他,圣域在更高的地方。要爬过高高的阶梯。而且只有女神忠诚的信徒才能拜访。而像他这样的小老鼠,更适合黑鼠窟。 这并没有什么难的。他的父亲就不是个高贵的人,对他的小偷小摸也不阻止。所以他加入了这里最大的扒手集团。里面都是些和自己差不多处境的孩子。他们就像是一群饥俄的老鼠,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抱团在一起生存。 但他从未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兄弟。这里也没有兄弟和亲人。 这里似乎是个和家乡没有什么区别的地方。少年阿雷每天早上站在阴影里,看那些穿着整齐的人携家人或朋友去大圣堂做祷告。他们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孱弱得如同绵羊。他想。然后挑选那些人中看起来最有油水的一个。 这里也是个没有未来的地方。他们从不思考未来,如同这里的人们从不思考自己为何出生。一切都和他的家一样。 后来他不再偷窃。因为年龄太大,体格强壮。他开始从事一些更加方便的工作——比如杀人或者替人收债。 阿雷喜欢在凌晨时分完成工作,因为那时候他可以轻松地哼着歌,看晨曦慢慢照亮大圣堂的宏伟屋顶。他喜欢那金灿灿的阳光发光的样子,让他想起金子,想起母亲关于圣域的说法,还有他小时候听说过的那些传奇故事。栩栩如生,但却遥远。适合每天的清晨和夜晚想象一下。 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会因为衰老而失误,会让手中的刀子滑落。黑鼠窟很少有老人,他们都早早因为衰老而付出了代价。而等待他的只有尖刀和绞索。在绞绳套上他的脖子时,越过人群,他看见远处大圣堂上一群鸽子正飞向更远处圣域的方向,那座他从小耳闻,却从未亲眼见过的喜乐之城。母亲说,在女神的庇护下,没有人会孤独和不幸。而他,现在就要前往女神的怀抱了吧。他感觉到脖子上绞索勒紧。女神会去爱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吗。她会拯救根本不值的拯救之人吗。他对此感到好奇。 这就是我的一生吗。 这大概就是我一生的故事了吧。大家不都这样吗。在庸庸碌碌活着的时候,偶尔看一眼圣堂的尖顶。然后排着队走向坟墓。 …… “哥哥?”他一瞬间以为自己在做梦。然后才发现了那张熟悉的脸——虽然那张脸蛋也又枯槁又憔悴。但他认出了那双金色的眼睛。 随即他发现自己的视线如此不清晰是因为被自己的眼泪所遮蔽。 “洛克斯……?”他才发现自己的嗓音沙哑又尖锐,差点连自己都认不出这把声音了。“我……我做了个可怕的梦。”一个孤独,但是又真实的梦境。他想。这是另一个我,这是少年阿雷的故事,兴许也曾是阿莱谢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某个棱角让他心里极为不舒服。他突然觉得并不是自己要来救洛克斯,也许只是为了和洛克斯重逢,来救自己…… “你的头发怎么了?”明明自己都不成样子了却还是努力摆出一副小大人的姿态的洛克斯,让法泽雷尔找到了日常的感觉。就算箴言剑眼下不在他身边——他渐渐回忆起来,被突然从身后捉住,然后见到了“裹尸布”,那男人的眼神里某种仇恨令他颤抖。然后他们收走了他的剑。并且用一桶冷水把他头发上的染料洗掉了。 他能想象自己现在看起来一定是一团糟。 “我自己剃掉的。”他努力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表情。就好像他们现在所在的不是黑暗潮湿的石牢,而是在父亲的书房里,神使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之间悠闲的对话。 “……笨蛋。这下你自己也被捉进来了。”洛克斯·费特看了看他,似乎早就预料到自己的哥哥没来得及去报信。 “没办法嘛,他们说如果我不跟来,就没有机会再带我来了哟。”法泽雷尔挠挠头。 “爸爸和索沃尔主教会狠狠教训你的。” “我亲爱的老弟,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啦。记得吗,老爹他啊,有一年夏天发现我们两个下河里摸鱼的时候气得都跳起来……” 他发现提起父亲的时候,洛克斯努力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金发的男孩努力控制着颤抖的嘴唇和肩膀。 这个笨蛋弟弟,明明遇到了很不妙的事情,却故意要把气氛搞得如同往常一样。但是在地牢里这样才是不正常吧? 法泽雷尔没有再说下去。他轻柔而坚定地抱住了自己的兄弟。感受到对方的双手也牢牢箍紧自己的后背。就好像回到了这样冬季的夜晚,他们相互簇拥着躲在被子里取暖的样子。法泽雷尔记得自己出来的日子并不长。但是为什么回忆起这些事情来却像是过了一整个人生那样遥远? “我们一定会回到父亲身边的。”最后他说,摸了摸自己兄弟柔软的金发。 “必须想办法通知星士……”洛克斯擦了擦眼睛,似乎情绪恢复了很多,“那个‘暮星’有问题。他……可能不是人类。” “……那他居然还让我们活着?”法泽雷尔说。 “他们说有一个针对我们的计划……”金发男孩回答道,“阿莱谢没有告诉我……” “角斗。”法泽雷尔平静地说。“那男人要我去参加一场角斗。就在我被他捉住的时候,他已经把条件告诉了我。” 法泽雷尔想起来,在跟随猩红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偷偷溜了出来寻找关押自己兄弟的牢房。但是这里的甬道纵横复杂,还有人巡逻,他只能缓慢地移动。直到他在某条无人的走道尽头被裹尸布堵个正着。 “这一开始就是个陷阱。”法泽雷尔回答他的兄弟。 “欢迎来到地下王国。”法泽雷尔回忆起那个男人空洞又冰冷的声音在地下的甬道里回荡起来,男孩抽剑转身,却被一长一短两把利刃同时指住了咽喉,势成剪喉之姿。 “你最好别动,小老鼠。”那个男人说。法泽雷尔发现对方有一张过于年轻的脸,而且……他也有一头和自己一般的银色头发,甚至连眼睛的颜色都一样。如果不是如今的情景,他或许比洛克斯更似自己的兄弟。 “裹尸布。”他说。 “法泽雷尔。”对方回答。 仿佛他们早就应该如此认识。
猩红和其他血鸦早有准备地从暗处移动了出来,他们利落地夺走了法泽雷尔的剑。然后将他双手反绑在身后。 “看来你经过了精心的准备。”裹尸布伸出一只手抓住法泽雷尔的短发,男孩感到脑袋上一阵抽痛。 随后一桶冰冷的水就从头浇下,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地上的积水里已然混合着染色剂。 “这样才符合你原来的样子。”那个被叫做裹尸布的男人冰冷地说。“女神在地上代言人的儿子,你不适合扮演一只老鼠。” “我弟弟呢。”他终于不用再扮演男孩雷尔。不用扮演黑鼠窟的孤儿。 “关于这个,我和我的兄弟对你们有更好的安排。”那个男人说。 “我想看看他。”男孩说。 “是的,我当然能理解。”他看见裹尸布的眼神里升起某种强烈的厌恶,那厌恶却似乎超乎了普通的仇恨,“一个好哥哥?你很乐意当一个好哥哥吧。”他的语调冰冷又疯狂,“好的,好的,小子。你会得到一个机会。你听说过角斗吗?” 法泽雷尔听说过这个词。但他以为这并不会发生在尼恩格兰这样的地方。
“很惊讶是不是。生活在离你这么近的地方。有那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裹尸布微笑起来。“小子,明天你就会有机会在你弟弟和众人面前扮演一次你的好哥哥的角色。我建议你,用尽全力。” 在男孩还未反应过来之前。他突然感觉后颈一痛。他能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那男人说:“把他拖去关他弟弟的牢房。” 这是某种仁慈吗。男孩在昏过去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就是如此。 然后他便梦到了那个刺痛他的梦。关于那个孤儿阿雷的一生的故事。在梦里他是阿雷,也是裹尸布,也是所有黑鼠窟的孤儿少年。 那是一个没有未来,孤独冰冷的梦。 “明天会有一场角斗。”他告诉自己的兄弟。看那双金色的眸子渐渐收缩。 “你不能去!”那双手抓痛了他,但是他没有介意。“你不能去!会死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弄死!”他头一次见到自己的兄弟这样恐慌,语气里几乎恢复了这个年龄的男孩才有的哀求和固执。“你会死的!”
我当然知道,我又不是真的笨蛋啊老弟。 “不,我不会死掉的。”他说。“金色风暴和索沃尔大人教给我的足够应付,女神则会庇佑着我们。父亲说过,无论在多黑暗的境地,女神都会看着她的子民。”她真的会看着这地下王国吗。如果她在看着,那么为何这世界上又有这么多的哭声?然而法泽雷尔知道这会儿不是思考这些的时候,不然他可能真的会因为害怕而陷入抓狂。如果他的精神崩溃,他的兄弟也会更加绝望。不行呢。至少这家伙不适合这样的表情。 “洛克斯·费特。”他试着像父亲那样的语调喊他的兄弟,“我向女神发誓,我会赢得角斗。并且不会死。我发誓。”他尽量不去想象明天可能就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天,不去想象尖牙撕裂自己血肉的痛楚。他很害怕。甚至感到自己整个身体都要颤抖起来了。他从未想到过死亡。他曾问他父亲,骑士们是如何克服在于恶魔作战中的恐惧。“我的儿子,那是因为他们除了心中怀有女神的荣光,并且相信自己的长剑受到骑士的祝福之外,他们也为彼此而战。”他的父亲说:“星士也是这样。你知道的,星士们成双行动。作战的目的除了消灭敌人,更多的时候,他们都为了能让自己的搭档活下去而战斗。” “您也曾有搭档吗?”年幼的银发男孩问。 “是呢……”神使回答,“星士的搭档都是可以互相托付给对方后背的人。人类只有互相支撑的时候,才会变得更强。当你拥有想要保护的东西时,你会变得比平时更勇敢。”
而如今,他只是想保护自己唯一的兄弟而已。因此他拍拍弟弟的肩膀,做出满不在乎的表情,这甚至迷惑了他那聪慧的兄弟。 希望他明天看到我被撕碎的样子,可千万别吓得大叫才好。法泽雷尔想。今晚他们最好还是不要回忆关于父亲的话题了。也不要去谈论明天。 他不记得自己和洛克斯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不过醒来的时候洛克斯还抱着自己。地牢里比地面上还要寒冷,连法泽雷尔也冻得发抖。然而他实在是太累了。加上见到了兄弟的放松感,很快他就睡着了。以至于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入睡的了。 醒来后没多久他就又被带走了。虽然他们进行了反抗,但是还是被分开了。法泽雷尔尽量使自己平静地看着弟弟,这也许是他们能这样对视的最后一眼。他在脑海里深深烙印了弟弟的样子。 之后他被两名血鸦押到了一间黑洞洞的窄室。这里一股霉味。那两人把他粗鲁地丢进去,然后立刻关上了门。 不久,他听到了外面轰隆作响的喧闹人声。 他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人声。一瞬间法泽雷尔以为自己身处于节日庆典,街头的尼恩格兰就有这样的喧嚣程度。然而眼下的喧嚣又不似庆典那样欢乐。他听到有个男人在咆哮。有好多个尖锐的声音发出奇怪的欢呼声。这喧嚣声中夹杂着“死!!” “去死吧!”的呼喊声。男孩感到浑身冰冷。这就是角斗吗。 “你很害怕吗。”他突然发现裹尸布在他发呆着倾听外面的时候走了进来。但是这间屋子太过昏暗,他回头,却看不见那男人的脸,面前只有一条窄缝透露出一丝光亮——那好像是在法泽雷尔面前的一扇门。 “我才没有害怕。”他尽量做出老成的样子,脑海中浮现出洛克斯的样子。学习那小子的说话方式。他对自己说。 “去看看吧。”裹尸布在黑暗中说。 他指的是那条细细地透露进光的窄缝。
那是一扇简陋木门的门缝,门似乎是从外面被锁上的。但是透过门缝。法泽雷尔看到了角斗场——这间屋子原来就在场地的底部,正对着角斗场地。而那些粗糙凿出来的石头看台上,早就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四面点起了火把,将这地下巢穴照耀得灯火通明,而火光摇曳,使得人群的影子又在石窟壁上印照出更多狭长而晃动的影子,一时之间这里仿佛就是阴影和喧嚣汇集之地。 他能看见观众们在看台上狂热地呼喊。大叫着下流的语言。显得极其兴奋。他还看到很远的地方,坐着一名有着金发的男人——那头金发在火光下显得如此突出,在这肮脏和疯狂的人群中居然显得有一丝圣洁——那应该就是‘暮星’,而他的弟弟,他隐约看见在暮星的身边,有个小小的身影,被那个叫做巨杉的高大男人按着坐着。他真的好小。法泽雷尔看着洛克斯想。他不能死在这里。不能死在这里。 “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听见自己喃喃地说。眼睛却离不开那亢奋的人群。 “为什么要有绞索呢。”他听见他背后传来裹尸布的回答,和昨日的不同,这声回答居然流露出些许的忧伤。 “小子。因为这和你们在绞索前所做的没什么不同。”那个声音继续说,“人们渴望正义,我就给他们血鸦。人们渴望审判,我就给他们匕首。人们渴望鲜血和死亡……于是,我给他们这个。” “在阳光照耀的地方,那些穿着金罗绸缎的人们不也这样娱乐吗。坐在最好的看台上看一场绞刑或者砍头。”裹尸布戏谑地说,“你没发现那些人和苍蝇一样痴迷于鲜血吗。我们在黑暗里设立的,不过是地面上那些世界的翻版而已。” “如果我赢了。”法泽雷尔没有回头,“你就放了洛克斯对吗。” 背后传来一阵沉默。 “你会死的。小子。” “不,我不会。”我答应过那家伙,如果食言的话,他一定会唠叨死。“但是我需要我的剑。” 他听到一个重物掉落在脚边的声音。那是箴言剑。 “嘿。你还真是个怪人呢。”银发男孩笑着拿起了自己的剑。 “有了这把剑你才是神使的儿子。而不是哪个随便捉来的小鬼。不是吗。”裹尸布在他身后说,“去吧。走向你的命运和死亡。让他们看看女神究竟会不会庇护她地上代言人的儿子。如果她还能看见这地下深处的话。” 那扇门徐徐打开。强烈的光倾斜进来。法泽雷尔微微眯起了眼睛。他能闻到场地内陈年的鲜血,灰尘的味道。这些都是之前的牺牲者留下的气味。男孩的出现似乎点燃了场上的气氛,意识到角斗就要开始的观众们爆发出更加响亮的呼喊声。虽然看不见,但法泽雷尔直到看台上的暮星正在打量自己。
他握紧了箴言。皮革的质感和剑身的重量令他感到安心。 法泽雷尔看到场地对面还有一扇门。那扇门用铰链锁紧,此时绞盘转动,门向两边打开,还未等门全部打开,就从那黑暗中窜出一条黑影。 那是某种比犬只还大的魔物。法泽雷尔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魔物。这只东西浑身漆黑,比普通的犬还要大上一圈,有着如同火钳一般光泽的利爪,和异常发达的犬齿。在法泽雷尔打量它的时候,它也在打量着眼前的男孩,估量着猎物。 在你和敌人第一次交手时,第一击是最危险的。
男孩想起了他的老师教过自己的那些技巧。那些在每个清晨,他都熟练地练习的技巧。法泽雷尔感到握着剑柄的手心在缓慢地沁出汗水。没关系的。虽然是魔兽,但是它只有一只,而且它不会比金色风暴大人更难对付。他想。他们认为我是个锦衣玉食长大的男孩,这把剑只不过是把玩具。傲慢是人类和恶魔都有的弱点。他的父亲曾这样说。“傲慢能使你失明。” 他看到那只魔兽低声咆哮一声,开始缓慢地移动脚步。它的利爪踏在石头地面上,划出细小的凹痕。法泽雷尔不敢怠慢,也随着它的移动而移动。始终让自己的正面对着那头野兽。这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在跳舞。男孩想。
魔兽和雷尔围绕着场地中间的某一点缓慢移动。他能听见观众席上的怒吼和下流话。有个男人说“上啊!吃掉他!撕碎他!” 这就是女神脚下的城市的人们吗。法泽雷尔的心里划过某个梦境,在梦里,他一生都在华丽的大圣堂的阴影下遥望圣域。 “阳光越是强烈的地方,黑暗越是如影随形。”他想起自己红发的导师这样说过。 然而眼下并不是感叹的时候。出于某种长期训练而产生的直觉,法泽雷尔突然发现那头魔兽的步履发生了变化,仅在一个心跳的时间,那团黑影突然收缩,如同一只猫那样弓缩起身躯。要来了。那团由尖刺和利刃组成的黑影突然伴随着一阵可怕的怒吼,夹带着一阵腥臭的风向他扑来。 法泽雷尔的右手比他的意识还要快速地行动——他抽出了箴言剑。冷冽的金属带出一道蓝色光晕瞬间与那团黑影绞作一团——剑刃和魔兽的利爪交叉,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那东西的身体沉重而恶臭,一下子就把法泽雷尔扑倒在地上。幸好箴言的剑身恰好挡住了它尖锐的爪子和腥臭的口腔。男孩顺势借力,在那只魔兽使用蛮力的同时抽出谶言剑滚到一边,他能感到自己脑袋后面那股阴冷的风划过,然而肩膀上却难逃利爪。他感到一阵尖锐的疼痛从背后传来。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左手还能行动,法泽雷尔没有时间去想那爪子曾离自己的脑袋有多近。 他滚了几圈,伤口摩擦在粗糙岩石地面上的感觉令他想要尖叫。
然而他才一抬头,就发现那只魔兽又一次扑跃上来。 蛮抗必将导致剑刃折断。如果是一把斧子的话,说不定还有机会。男孩努力一蹬腿,那东西又扑了个空。它被这追逐的游戏惹怒了,带着愤怒咆哮不已。声音和看台上的叫骂声混作一团,在整个地下角斗场内形成可怕的音浪。
那些咒骂和愤怒似乎刺激了它。它不再打量寻找下一个契机。又再次扑跃过来。 法泽雷尔没有移动,他想起金色风暴大人在一次训练中这样对自己说:“如果你遇到对手只会慌不择路地逃跑,那总有一天你会被堵住去路。孩子。唯一的办法是克服你的恐惧,面对它,观察它。” 于是男孩忘记了自己肩膀上的疼痛,他压抑住自己的恐惧,在那个极短极短的瞬间,他对自己说,世间万物皆有弱点。别让恐惧遮住了你的眼睛。观察它。不要逃避。 一切都是那么缓慢。“像个战士那样判断!”他对自己说。 它看见那双利爪上还沾有自己的鲜血和皮肉。那东西的表面看起来全都是如同尖刺一般的刚硬长毛,它发达精瘦的肌肉就在那漆黑色的毛皮之下,他能看到它们串连一气的运动。
“观察你的敌人。不要因为恐惧移开目光。不要让逃跑的念头控制住你。”他脑海里的金色风暴大人在回忆里这样说,然后男人挥动那把可怕的双手剑——那把剑毫无装饰且粗糙难看,但却是真正的杀戮机器。男孩还记得自己耳边划过的剑风。 “观察你对手的肌肉。你的对手也许可以迷惑你,也许可以恐吓你。但是他们的肌肉会出卖他们。观察他们的手和腰,还有腿。看它们绷紧蓄力的样子。不要选择逃跑。要学会攻击。孩子。” 他于是看到那一连串黑色的肌肉起伏如同海洋。 让利剑化为你的双手。调整你的呼吸。 他忘记了自己肩膀上的伤痛,也不再听到看台上的喧嚣。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圆圈,圈内是他和它。银发男孩放低重心,那东西如同一枚接近中的长剑。他稍稍侧开自己的躯体,这样一来他便将自己的胸膛完全暴露在那野兽的身前。 来吧。来吧!他突然感觉自己热血沸腾起来。来吧你这野兽! 那团黑影中有两点精亮之火,如同流动熔浆。它果然迫不及待地改变轨迹,朝他的胸膛扑来。那魔兽以一种动物才能完成的角度朝他伸出尖锐利爪。如同魔女的尖利手指。 他以剑为杖,驻于身后,一个下腰躲过了这一击。 它一个扑空,落地时分便没有站稳,在一刹那间站立不稳。 男孩并没有兀自离开,而是折返身形,抓住这个宝贵的瞬间,递出他的第一次攻击。 从箴言上传来了令他脑袋发麻的触感。 他从未杀过人,甚至没有用这把剑伤害过任何动物。法泽雷尔漫长的训练时光中他唯一的对手是金色风暴大人的巨剑和木桩。 箴言在那坚硬的刚毛之间划开一个伤口,而那些刚毛同时也伤害到了法泽雷尔的双手。男孩不敢刺深,他在那魔兽愤怒地还击之前就抽回了自己的剑,退开到一边。 看台上发出了混杂着愤怒和惊叹的吼声。比刚才更甚。 那怪物被伤到后更是狂怒不已。 一瞬间,轰鸣的声音又回到了法泽雷尔的耳朵里。他感到自己的心脏狂跳,而且感觉饿不到自己手上被背上的伤痛了。他瞥一眼自己手,它们被那些如同刀刃一般的刚毛弄得伤痕累累。好吧,比起被撕碎,这样要好很多。 那东西又一次扑来。这次他不再害怕。如同死亡之舞,他闪身避开那魔兽,虽然姿势匆忙又不好看,但是他躲开了。他发现自己可以从愤怒的魔物身上发现更多的破摘。它的每条肌肉,它的眼睛都在告诉男孩下一次要往哪里躲藏。 这不就得了。他金发的教官说。无论是人类还是魔兽当你的对手。当你战胜了自己的恐惧之后,你就赢了它一半。
于是这法泽雷尔主动上前,那东西尖啸一声予以反击。 男孩把那爪子和牙齿想象成是老师的练习剑。他用一记侧劈挡开了一只爪子,然后立刻反手用另一边挑拨开它的牙齿。然后他看到了那块地方——这怪物愤怒地直立起来想要用体重和身高压倒自己的时候,在那一瞬间他看到了它柔软的腹部。没有刚毛。颜色稍浅。 送它一条胳膊吧。
法泽雷尔驱动谶言剑向下直刺那怪物的柔软小腹,同时他感到自己脸上溅上自己的鲜血——真奇怪,疼痛来得如此缓慢。倒是在那一刻,他还以为有人把一桶热水朝自己扑来。随后他才几乎在自己的利剑刺进那怪物的小腹同时,感到自己左边身子疼得如同被火焰灼烧一般。 他听见看台上有个女人发出尖叫声。 他感到自己的脸颊上湿湿黏黏。不知道是那怪物的鲜血还是自己的鲜血都糊在了自己的视线上。好臭。他觉得自己快要呕吐出来。 左边肩膀疼痛难忍,他能清晰地感到三道灼热的伤口在背上炸裂开来。——在他扑向那怪物的怀抱时,一定是那怪物的爪牙留下的这些。 我本来以为我会失去一条胳膊。事实上在那个瞬间他并不知道这只野兽是否注意到了自己的动向。如果它更快一些,就会咬掉我的胳膊。 那样的话老爹就不能罚我刷洗锅碗了。独臂男孩要怎么刷洗呢。 他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这个念头。 箴言深深切入了那怪物的身体,法泽雷尔在那东西尖叫着要蜷缩起来撕咬他脖子之前使出最后的力气将箴言从下到上一口气拖拉拽动。剑身在那东西的肚子里搅作一团。恶臭伴随着鲜血扑鼻而来。他一脚蹬开那具魔兽的身躯,同时自己也向后重重摔倒。 那东西在自己的黑血和内脏里挣扎抽搐,但早就没有了嘶吼的力气。 在另一边的男孩觉得自己的心都要从胸口炸裂了。
好热。他只有这一个念头。这里怎么如此炎热。法泽雷尔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液。女神保佑,左边身体并没有失去行动能力,那怪物显然在要咬断他筋骨之时耐不住疼痛而松口——更重要的是,它想要调转自己的头颅去撕咬自己身体下的男孩的脖子。 看着那怪物抽搐着咽气,以及看台上爆发出的不满和咒骂声。法泽雷尔突然想要大笑。他知道自己现在看起来一定可怕极了。所以他抬起头,往暮星那个方向看去。他看不见那男人的表情。他也不在乎。男孩大声笑起来。然后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法泽雷尔感到自己浑身酸胀。似乎刚才无穷的精力都已经被用尽一般。但是他还是站了起来。向观众展示自己还活着的事实。 这是我所收获的第一个死亡。 但它却能让我和弟弟活得更久一些。 “放了他!”法泽雷尔在喧闹中朝暮星的座位喊道。“放了我弟弟!你们这些该死的混蛋!我活下来了!看到没!我杀了你肮脏的宠物!” 他看到暮星从座位上站起来。 你要毁约吗。 比起抛弃了世人的女神,丧失了信用也不能让你有任何收获。 然而法泽雷尔突然发现了气氛的异样。男孩回头。发现裹尸布正从那扇他登场的入口处走了过来。他的手放在自己两把剑上。 “现在你可以放了我弟弟了。”法泽雷尔说。 “刚才那是你为自己赢得的。”男人说,言辞里有一种跃跃欲试和自负。 “现在你要为你弟弟赢得回家的机会。而你的对手,将会是我。” “这不公平!”法泽雷尔朝他喊。 “很公平。”那男人说。同时他回头对身后跑进场地的红发少女说,“别过来,告诉我哥哥,没有我的同意,就算是他也不能碰这两个男孩一根汗毛。替我告诉巨杉。我要那个金发的活着。也告诉我哥哥,让他呆在看台上。” “可是阁下,这不是……” “这不是我哥哥的计划。他的计划已经结束了。”裹尸布回过头来,法泽雷尔发现那双蓝眼睛正盯着自己看,那男人说“现在是我的计划。让我们为各自的兄弟而作战。如果你想要回你弟弟,那么我必将成为阻挡你的阻碍。”他抽出那把造型别致的苍白利剑,“看见没?这很公平。为了我们的兄弟。”
那红发少女沉默地后退,然后回到了角斗场的入口处。她对侍卫说了点什么。 看台上的观众发现他们的裹尸布大人亲自下场挑战这孩子,似乎也无比满意这样的发展。没有人提出异议,气氛如同刚才的角斗开始。 法泽雷尔看着他,“很公平。裹尸布。”男孩拿起了箴言剑。 左肩抽痛,双腿酸胀。但是他不能死在这里。尤其是自己活着,而洛克斯死去。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在这时。一阵猛烈的爆炸撼动了整个地下角斗场。 火把剧烈晃动起来。而角斗场内瞬间充满了呛人的烟雾。在法泽雷尔还未反应过来之前,他就听见了兵器相交的声音。还听见有个人喊着“是圣域的!”“有入侵者!” 男孩呆立在哪里,怀疑自己的耳朵。
他曾经想过再也不会见到这些穿着法祭和星士袍子的人们了。在他向红隼告别的那个时候起,恐怕他的内心深处就在低声念着永远的告别。 他发现烟尘和混乱里冲入了许多身影。而法泽雷尔还来不及辨认,就看见裹尸布返身离去。他一定是去找他的兄弟了!我这个笨蛋在发什么呆,洛克斯还在他们手里! 此时整个角斗场已经成为了刀剑和星魔法的战场,陷入了一片混乱,恐怕整个地下矿洞都是这样了——圣域的增援不知从哪里发动了奇袭。但是这样的混乱中,他们都不知道洛克斯还在那暮星的手里。 跟着裹尸布! 法泽雷尔试图在一片混乱中找到那个银发的身影。 “你在找什么。”火焰和烟雾里突然出现一把匕首。直指男孩的鼻梁。 是那名有着不可思议红发的少女,烟雾和尘烟像水流一样从她的身躯边急速退散而去,使她看起来居然带有几分史诗般的美感。 “裹尸布!”法泽雷尔怒吼一声作为回应。用箴言一把劈开那挡住自己去路的匕首。 “我不会让你接近阿莱谢大人的!”少女一记突刺,动作快得像条毒蛇。法泽雷尔瞪大双眼。 直到金属相碰的声音响起。 那把匕首戳上了一面厚实的钢铁,碰撞之下居然冒出火花来。 “小姐。男孩终究不过是男孩。”有个爽朗如雷的声音在法泽雷尔头顶上响起。男孩感到自己身后强烈的存在感。没错。能够给与别人如此感官的只有那一个男人而已。 “不如由我替代我的学生来和你共舞一曲如何。”金色风暴爆发出一阵大笑,猩红警惕地看着法泽雷尔身后走上来的这个男人。只见他双臂如同双蛇般灵巧舞动,将那把巨大的利剑舞得居然如同妇人的轻盈羽扇。然而呼呼刮过法泽雷尔耳边的风声,和他们四周立刻散去的烟尘则清楚表明这钢铁怪物的庞大重量,——这把剑根本连剑都称不上,形容它是一把粗暴的钢板还差不多。 然而金色风暴只是灵巧地舞动它。仿佛一位舞会上的绅士炫耀自己的新手杖。最后它发出沉闷可怕的一声。被双手持柄矗立于地上。 少女如同猫一般弓起身子,小心翼翼地估算自己和敌人之间的距离。眼神里充满了敌意。
“现在,去找你要追的那家伙。”从法泽雷尔前方的高大背影那里,传来这样的话语。 “金色风暴大人……”法泽雷尔犹疑了一下。 “别死。” 然后男孩便转身跑了起来。他听到背后传来猩红愤怒的尖叫,她想上来阻止我,但是金色风暴大人挡住了她的去路。那个男人很强。法泽雷尔想。他不会有事的。 法泽雷尔不记得自己在互相交战混乱的人群里跑了多久,地下坑道里满是烟尘。他只能玩下背脊尽可能贴着墙壁走动。他们走不远的。他想。这里有那么多的法祭和星士。裹尸布和暮星走不远了。他四下张望。 他见到无数尸体,有星士也有血乌鸦,这地下矿坑居然犹如地狱一般疯狂。 他还看见有个法祭身负重伤还在战斗,他大喊着女神的名字。但法泽雷尔知道他并不是为女神而死。女神没有让他们去死。这些人都是为了救我和洛克斯。 他们为我而死。 他闭紧眼睛,强迫自己寻找那银发的身影,不再去思考其他。 那一抹银色在人群里。当他追随着它来到地面上的时候,发现此时已经是夜幕降临的冬夜了。冷冽的风夹裹着稀疏的雪灌进了满是烟尘的甬道。法泽雷尔爬出来的时候,发现这里是树林里的一处暗门。空气阴冷而凝重。快要下雪了。 他知道他就在那里的黑暗中等待。 所以就在雪花开始飘落的时候,法泽雷尔看到那个身影从黑暗里走出来,男孩也没有尖叫。
今晚虽然有雪,但光线似乎不错。他甚至能看到雪花飘落到对方那华丽的银发和黑色皮甲上面闪闪发光的样子。如果我的头发没有剪短,男孩想,我们会更加相像吧。他毫不怀疑在这样的大雪里,法祭和星士会将他们搞混。 他也明白我们的命运会在此做个了断。男孩想。然后他沉默地拿起自己的剑。 只有打到他,才能继续追击暮星。 雪花纷纷落下,时而被风吹动,如同无数银光飞舞。而男孩和男孩只是相对矗立。法泽雷尔能看到裹尸布手里同样也拿着两把剑。他知道那是一长一短两把苍白利刃,如女巫指骨般消瘦。
他们同时跑向对方。 女妖和挽歌双双咬上箴言。相交,分开。相交,分开。相交,分开。金属发出锵锵哀鸣。法泽雷尔只看到那双蓝色的眼睛在每次靠近时候望着自己,那眼神里充满仇恨,悔恨,痛苦,和……悲伤。
我看着他的眼神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男孩努力辨识在雪花之中划来的利刃。判断对方每一次的进攻方向。寒冷和激动让他忘记了背上的痛楚,也忘记了疲惫和恐惧。
裹尸布的身高优于法泽雷尔,他用身高和力量压制着神使之子。而法泽雷尔则比他还要快速和灵巧,他使出了所有学到的招数。威逼利诱,一寸一寸地夺取他们之间那一点点空间。每当女妖和箴言相交,总会迸发出一阵火花。这两把剑,一把苍白如雪,一把浑厚而坚实。它们无声得劈开空气,劈开法泽雷尔和阿莱谢呼出的白色雾气。 两个男孩从森林里一直打到森林之外。有时候法泽雷尔眼看着就要勾到对方的衣衫,但是裹尸布却用两把剑死死防守。 远处忽然想起一阵巨响。 然后法泽雷尔看到火焰和闪光同时从森林的另一头亮起。一瞬间,少年以为是晨曦从树林间亮起——那是法术的作用带来的光亮。 “洛克斯……!”当光渐渐暗下的时候,法泽雷尔发现自己一步也挪不开腿了。那一定是裹尸布带着洛克斯逃走的方向! 他清楚地知道弟弟一定会想办法脱身。但是……在这样的雪夜中使用魔法和恶魔对抗,银发少年无法想象自己的兄弟面对的是怎样的情况。他感到自己的呼吸紊乱且急促起来。 “你在看哪里。”挽歌以一记凌厉的攻击划破了法泽雷尔的脸颊——如果不是少年及时向后跳跃逃开的话,他的耳朵恐怕就保不住了。而在那里的裹尸布则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持续逼近着。法泽雷尔只能举起箴言抵挡。他感到每一次阻挡,自己的双手就会震得发疼。 我还是太弱了吗。少年想。裹尸布完全没有把注意力浪费在刚才的动静上。 难道他不担心自己的兄弟吗。 “你……你知不知道你在帮恶魔!”法泽雷尔一边努力控制自己的气息一边调整着步伐。积雪和寒冷以及强敌都在消耗他的体力。 “你是不会懂的。”裹尸布侧身一击,长短剑交替着轮流进行进攻和防守。“生活在圣域的你懂什么!” “我……”银发少年艰难地发现自己居然无从反驳。
洛克斯从来没有遇到过危险。除了这一次。在圣域的日子,与其说相依为命,不如说因为身份特殊,所以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所有的黑暗和绝望最多不过是书本上的几个词汇。合上之后,他们有温暖的羽毛床垫和温热的睡前牛奶。从不知道有人会因为在临死前还得不到一碗米粥而绝望,也不知道曾有个哥哥为了救出弟弟而成为恶魔。 “恶魔最喜入侵那些脆弱的灵魂。恐惧,绝望,嫉妒,愤恨,都能削弱灵魂。”少年记得自己的父亲如此说,“因此你也要观察自己的心灵,吾儿,绝对不能让这些情绪主导你的灵魂。” “那我要怎么做呢?”他记得年幼的自己这样说 “成为更……优秀的人。”父亲温柔地摸摸他的银发,“成为足以守护住所珍视之物的人。吾儿,优秀和强大并不是指坚不可摧的武力,甚至也不是指聪敏的智慧。没错,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见过太多的星士和人类,虽然拥有强壮的体魄和高超的智慧,仍然被恶魔所诱惑与控制。” “那么什么样的人称的上优秀?” “那是在希望泯灭之时仍然心怀正义,明知道前路上等待自己的是死亡,愧疚并认知于自己的愚蠢和无知,然而战胜这一切,仍然前进的人类。”父亲曾经在那天的阳光中对法泽雷尔这样说道,“那才是女神希望我们成为的人。拥有一颗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打败的灵魂。”
法泽雷尔忘了自己当时是如何回答父亲。也许是根本没有回答他。那时候他还是那么幼小。他的世界简单明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法泽雷尔发现他的话居然令裹尸布有了一瞬间的犹豫,“对不起……”女神阿,如果你在看着的话,就让我来行使您的意志吧。 法泽雷尔突然扬起一脚将地上积雪扫起。裹尸布淬不及防用双手遮挡眼睛。“!!!” 然后仿佛再没有这样的机会。法泽雷尔用尽力气向阿莱谢劈去。 一阵寒光和刺耳的尖啸。伴随着衣帛撕裂的细微声响。 挽歌应声折断成两截。而女妖也被震落在地。 手指上传来可怕的触感,但是法泽雷尔没有退缩。我什么也不知道。他发现自己居然在流泪。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我能做的,就是活下去,找到我的兄弟。少年卯足全力扭转自己手中的剑柄。自己的虎口也传来撕裂的痛楚。 他看见阿莱谢倒下。真奇怪,他的表情不是惊讶,似乎还带着一丝满足。
银发青年的侧腹部正涌出鲜血,滴落到地上。雪地贪婪地吸收着他的血液,直到那里化为一滩黑色的水洼。 银发青年仰躺在地上,用一只手捂住自己的侧腹。却并没有哀嚎。在他身下,是折断的挽歌。而女妖则在一尺外。 法泽雷尔发现他居然在笑。但是血水却时不时呛到他自己。 “小子。”他沙哑地呼唤。仿佛刚才的怒意和憎恨在那一瞬间全都替换为了疲惫。 “是的。”法泽雷尔喘着气,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回应裹尸布,但他还是走了上去,单膝跪下,用那双蓝色的眼睛看着他。 “你接下来,……要去找……我哥哥了,对吧。”裹尸布断断续续地说,法泽雷尔能看见生命的光辉正在他的眼睛里暗淡。他要死了。男孩想。 “没错。”他回答。 “拿……走我的女妖。”裹尸布稍稍侧头看了看飞在远处的那把短剑。 “用它……替我……替我哥哥做个了结……”
法泽雷尔看着他,沉默地点点头。“你全都知道的。” “……因为那是,我守护住的,唯一的东西。”裹尸布微笑起来,他的脸开始随着失血变得苍白起来,“就算那是幻觉……但是……你知道……” 如果洛克斯有一天也……法泽雷尔发现自己无法想象自己会不会做出一样的举动。甚至连这个猜想本身都令他觉得恐惧。 “不要成为我……”这是法泽雷尔离开时,裹尸布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而男孩拿走剑之后,就放任那个男人在雪地里。我不想看他死。法泽雷尔想。不是胆怯,但是我无法看着他死。因此他快速地逃开了。一直朝刚才传来爆炸声的地方跑去。 当法泽雷尔来到那里的时候,却看到一片狼藉中只有那名叫做巨杉的巨人的尸体。若不是那庞大的身躯,他根本认不出是这个人了。因为尸体的面目像被巨大的火焰烧过那样扭曲而焦黑。而更远处,则是一群受伤的法祭和星士。在那群人的中心,有他熟悉的人——一头红发的索沃尔主教正抱着自己的弟弟,而洛克斯就像睡着了一样靠在主教怀里。他身上有许多伤痕,雪花很密集,法泽雷尔看不清主教的表情。 “洛克斯!”他跑起来。别死。少年没有喊出声,生怕这个词会像一句诅咒般应验。别死,我来了,求求你,女神。 不知为何,他的脑海里只是不断浮现出裹尸布临死前那虚弱的微笑。 别让我疯狂,求求你,别让我成为他。少年跑到索沃尔主教的身前,才发现洛克斯的胸口在微微起伏——看起来只是耗尽了力量而暂时昏睡着。 “你会吵醒你弟弟的。”索沃尔抬头冷酷地看了一眼几乎要哭出来的法泽雷尔。这个男人是真的生气了。银发男孩知道。今晚有多少人为我们而死。他胆怯地看着自己的老师。 “我简直没有收过更笨的学生。”索沃尔抱着洛克斯站起来,将金发男孩交给站在自己身后的皮肤黝黑的侍卫亚伦。然后用那双蓝眼睛看看法泽雷尔,接着索沃尔抬起一只手来。一瞬间,银发男孩居然有了一种想要缩脖子的恐惧。老师打我的话,也是没办法的。法泽雷尔想着,低下了头等待着。
然后那只手轻轻落在了他乱糟糟的短发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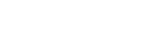









 楼主
楼主








 发表于 2013-3-7 11:35:18
发表于 2013-3-7 11:35:18














